中国有句俗话:“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句俗语看似平淡,但却蕴涵着丰富的哲理,实际上是对地理条件与人类生活两者关系的高度概括和凝练表述。不同民族的社会历史文化性格无一例外地都受到其所处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的影响与制约。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言,“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人们在创造历史、改变环境的同时,首先要受包括地理环境在内的前提条件的制约,人们不可能逾越这些既定的前提,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

图1-7 入乡随俗的印度人
印度社会历史发展特点和民族性格与上述印度地理环境及自然条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地理条件对印度社会历史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富庶性与文明的较早崛起。印度地大物博,资源丰富,广阔无垠的肥沃耕地、为数众多的滔滔江河与取之不尽的丰厚物产,为印度文明的产生创造了得天独厚的物质基础和有利条件,促使印度次大陆较早地由石器时代过渡到铜器和铁器时代,并进入阶级社会的文明时代,成为人类文明最早的发祥地和摇篮之一。
第二,闭塞性与发展的不平衡。蜿蜒的群山与深邃的海洋把印度次大陆与外界隔绝开来,使印度在地理上自成一体;印度半岛内部地形复杂,高原与低地,河流与湖泊、沙漠与沼泽,丛林与草原交错,交通不便,将印度分割成许多“一统天下”的地域小单元;印度气候温和,雨量充沛,物产丰富,人民尽管维持着低下的生活水平,但由于一般需求不大,又容易得到满足,从而不思改进生产工具、提高生产技术,导致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这更加深了社会的闭塞与停滞。
各地区自然条件的差异、地理上的相互隔绝,必然造成各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严重不平衡性。平原河谷地区,由于土质肥沃,雨水充足,适于农耕,兴起了发达的农业经济;高原、山地或者沙漠地区,由于土质贫瘠,干旱缺水,不宜耕作,经济十分落后,社会处于更为原始的状态。近代以后,沿海港口或通商都会,发展了繁荣的工商业经济,过着豪华的都市生活,而深山幽谷或密林深处,依然从事落后的畜牧业或农业耕作,过着原始而简陋的生活。
第三,分散性与政治上的不统一。一方面,地理条件的差异所形成的各个地域单元,有其各自不同的经济利益、文化习俗和政治意识,因此形成大大小小长期独立的政治单元和实体。在历史上他们争战不休,互相吞并,各自为政,独霸一隅。人们只有王国、地区甚至更小行政单元的概念,根本没有“印度”这个国家概念。在这些政治实体内,不管是百姓还是统治者,对印度国家的兴衰漠不关心,置身事外。而一些王公贵族则始终保持离心的割据倾向,一遇机会,便脱离有名无实的中央帝国,分裂自主,独立称王。
另一方面,幅员辽阔,山川阻隔,交通困难,使中央政权实现政治统一成为遥远的梦。权力重心偏于北方的统治王朝中央政权,为谋求统一,往往劳师动众,长途跋涉,不堪劳顿。即使武力暂时奏效,勉强统一,一旦撤军,叛乱又起,中央政权鞭长莫及,待中央平叛大军赶到,地方势力已经坐大,反为所败。因此,印度在古代和中世纪,政治上一直长期陷于分裂状态,如马克思所说,“印度斯坦是亚洲规模的意大利。在政治结构方面是同样地四分五裂。”
第四,重要性与外族的不断入侵。印度次大陆处于东西方交通要冲,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在古代,印度位于几个世界文明中心的中间,扼东西方丝绸之路及海上交通枢纽。在近代,印度是西方探查新航路的重要一站。同时,印度的地理位置和地形为外族打开印度大门准备了陆路和海路的便利条件:位于西北部的兴都库什山的几个山隘,如开伯尔山口、博朗山口和穆拉山口,为陆路入侵提供了孔道和门户。而辽阔浩瀚的海洋,则为海上入侵者的舟楫炮舰提供了航行之便,布满富庶港口的漫长海岸,为来自远方的勇猛海盗和冒险家的帆船敞开了大门。
资源富饶,经济繁荣,“黄金遍地,香料盈野”,为垂涎三尺的外族入侵者提供了诱因,内部的四分五裂和动乱纷争则为外族入侵提供了良机。于是,在历史上,一批批的外族便蜂拥而至,都想品尝和吞食这块具有取之不尽的财富的“肥肉”。从陆路入侵印度的外族有:雅利安人、波斯人、希腊人、大夏人、安息人、塞种人、阿拉伯人、匈奴人、突厥人、蒙古人、莫卧儿人等。从海路入侵印度的外族有:葡萄牙人、荷兰人、法国人、英国人等。
西北陆路交通要道不仅是外族入侵的主要通道,自古以来也是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的重要渠道。虔诚的香客与勤奋的商人通过这些山口往来穿梭于印度和其他国家,不仅带来了异域文化习俗,也把印度的东方文化传播到其他地区。
第五,神秘性与宗教的盛行。印度宗教盛行与印度“北背雪山、三垂大海”的地理环境有很大关系。
北部雄伟壮观、峰峦叠嶂、白雪皑皑的喜马拉雅山,东北部瘴气缭绕、毒蛇猛兽出没的阿萨姆原始森林,西北部既无鸟兽又无水草的塔尔沙漠和高山插云、雪岭延绵的苏来曼山和兴都库什山,在令人神秘敬畏之余又常常引发无穷的遐想。特别是喜马拉雅山被印度人视为神居仙游之乡,是无数圣徒香客朝觐巡游的圣地,围绕它产生了无数美丽动人的神话、故事和诗歌。
这些令人望而却步、仰之弥高的北部崇山峻岭,再加上东西南三面浩瀚无垠、神秘莫测的汪洋巨泽,给人们带来灌溉和舟楫之利而又常常肆虐成灾的江河,终年给人带来滂沱暴雨和难挨酷热的变化莫测的热带亚热带气候等,使处于远古时代生产力水平低下的人们深感恐惧和神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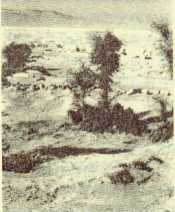
图1-8 西部大沙漠
在这种封闭而险恶的地理环境和无法驾驭的自然力量面前,人们感到宇宙的广阔和个人的渺小,需要寻求一种足以安身立命的依托,于是幻想着用祈祷、膜拜、献祭等方式来讨好主宰自然界的神灵,以获得恩惠与庇佑。因此,印度便成了孕育和滋生宗教的温床。
世界各大宗教都可以在印度找到立脚点,许多独特的宗教都可以在印度找到家园。婆罗门教、印度教、佛教、耆那教、锡克教发源于印度,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祆教、萨满教等在印度也拥有大批信徒。在世界历史上,很难找到一个国家像印度这样长期地笼罩在浓重的宗教气氛中。
第六,多样性与传统的持续。印度是一个具有浓郁而强烈的传统色彩的多民族、多种姓、多宗教、多语种的多元国度。印度古老的宗教信仰、婚姻制度、丧葬习俗、种姓制度等基本上都保留了下来。印度传统社会结构,特别是农村公社,在世界各民族中是持续最久的,一直延续到近代。这一特点与其地理环境也有一定关系。
北部高耸的喜马拉雅山区有2414公里长,如同印度北部的一道天然高墙和屏障,对印度起着一种保护作用。印度本身的地理构成十分复杂,高山、河流、湖泊、沙漠、沼泽、丛林、草原,给交通工具落后的古代人造成了交流的障碍,这些障碍把印度分割成不同的生态系统和地理单元,这些障碍构成了印度多种族、多语言、多宗教的地理基础。
地形的复杂,山川的阻隔,道路的缺少,行旅的艰险,无疑是造成农村公社封闭孤立的原因,农村商品交换困难,严重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村公社内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长期稳固地支配着整个农村社会,这又使得农村公社得以长期存在和延续。
地理条件对印度民族性格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尚会鹏先生对生态环境与印度民族性格做了深刻的分析,认为不同生态环境下的人,有不同的生活方式,从而形成不同的性格。一般来说,大陆型气候形成的民族性格,往往具有坚韧、忍耐、阴郁、难以捉摸、感情含蓄等特点。而岛国型气候下形成的性格,则具有积极、活泼、灵活、性急、毛躁等特点。当然,即便是同属于大陆型气候,各个国家乃至各个地区的人的性格也是有差异的。印度次大陆生态环境的特殊性,对印度人性格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印度人所处的自然环境较为严峻。印度次大陆属于大陆性气候,温差变化大,雨量不均,居民既苦于干旱,不断祈求天降喜雨,又苦于恒河泛滥,房屋倒塌,饿殍遍野。恶劣的环境磨炼了印度人,培养了印度人极大的忍耐力。
其次,印度的气候非常炎热。炎热的天气常常使人处于“半昏迷状态”,不想外出,不想活动,劳动欲望低下,只想躺下睡觉。在印度农村,到处可以看到躺在树荫下睡觉的人,外国人普遍感到印度人睡觉时间长。正是在这种气候条件下,产生了印度教徒的沐浴、斋戒、禁欲、瑜伽、冥想、林栖,以及耆那教的以天为衣等习惯。
最后,印度的夏季与雨季交错。在印度北部地区,夏季干旱,通常赤地千里,土地开裂。而雨季一到,又常常暴雨连连,江河横溢,泛滥成灾。年复一年,如此循环往复。面对这反复出现的自然现象,人们感到无奈、无力与无助,唯有敬畏和消极接受而已。恒河被印度教徒尊为圣河,至今仍是印度教徒向往的圣地。恒河中下游和北孟加拉地区也是佛教、耆那教产生之地。佛教和耆那教的轮回、解脱思想的形成不能说与这样的气候特点没有联系。
此外,印度的物产丰富。印度植物茂盛,物产丰富,充饥果实较多,人们无须太多努力即可饱腹。温暖的气候也可免除许多衣物,一些人一年到头腰间仅缠一块旧布。在生存问题上,对大部分印度人来说,“温饱”问题不难解决。相对而言,基本不存在“温”的问题,只存在“饱”的问题。


 不详
不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