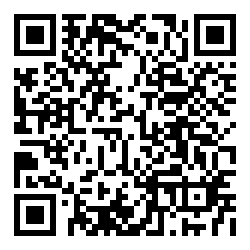在有明一朝发展到极致的“阳儒阴法”的社会统治技术,虽为我们帝国奠立和巩固了其坚如磐石的专制政治的统治,同时却从根本上挖空了国人赖以安身立命的精神的根基,使中华民族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信仰危机。这一点,“闻道尤切”的李贽这一中国优秀古代知识分子对之体会尤切。因此,当李贽为自己苦苦寻求其精神最终皈依时,他发现自己是那样孤立无助,是那样的走投无路。然而,在他几近绝望之际,他蓦地谛听到了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召唤的声音,这声音是那样的遥远,却又是那样的亲切,这声音是那样的微弱,却又是那样的深沉有力。这不是来自此岸的东土俗世的声音,而是来自彼岸的西方佛国的声音,这声音从他灵魂深处发出而犹如神谕:“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犹如在旷无人烟的深山里听到了空谷足音,犹如在无比喧嚣的闹市中听到了天外之弦,这声音引领李贽步入了一新的精神故乡。虽然这一故乡以其虚无缥缈看似“乌有之乡”,但却和李贽生活于其中的熙来攘往、声色犬马的世界形成鲜明对比,使李贽不能不为之怦然心动。这一新的精神故乡,就是李贽在晚年深深涉足于其中的佛教领地。1588年,李贽已年届62岁,也正是在这一年,他在麻城芝佛院剃发为僧,一了其所谓“吾谓当此时,正好学出世法,直与诸佛诸祖同游戏也”这一心愿,318并真正兑现了他所谓的“欲真实讲道学”的人,就“断断乎不可以不剃头做和尚矣”的人生诺言。319
这也许是李贽一生中最富戏剧性之举。称其为戏剧性,不仅是因为他早不出家,晚不出家,直至62岁才出家这一做法令人不可思议,不仅是因为他所谓“则以年纪老大,不多时居人世故耳”这一解释难以自圆,并且更重要的是因为其出家为僧之举,实际上和他一贯持奉的人生理念是那样的极其冲突、不无抵牾。正如他曾经告诉人们的那样,“余自幼倔强难化,不信学,不信道,不信仙释,故见道人则恶,见僧则恶,见道学先生则尤恶”,320李贽生性就远佛恶僧;也正如他在信中对朋友一吐胸臆的那样,“我岂贪风水之人邪!我岂坐枯禅,图寂灭,专一为守尸之鬼之人邪!何必龙湖而后可死,认定龙湖以为冢舍也!”321李贽曾明言他不以佛舍为其生命归依。“尔非陈仲子,我岂老瞿昙”,322一语道破心语,无论是“道”还是“释”,都和李贽扯不到一起。然而,这一切并不意味着李贽出家为僧并非其真心之举,并不意味着李贽出家为僧仅为暂借佛寺以栖身的权宜之计。正如李贽发自内心深深厌恶当时的“道学”一样,在其真心向佛这一点上,也是有目共睹而毋庸置疑的。他自称“居士”“卓吾和尚”,以所谓“化外之民”自诩,323并长期隐居龙湖,生活在佛寺“芝佛院”里;他抱病编写《法华经》讲义,抄录前辈禅师的好诗好偈,集成长达数百页的《释子须知》;他在佛寺与佛门弟子朝夕相处,宣讲佛经,切磋释理,使无论男女的当地真心向佛之人,无不对其靡然宗之并膜拜顶礼;他作《豫说戒约》,为其弟子严申佛院规约,如山门礼仪、佛灯钟鼓、守塔祀典,以及佛门修行的种种清规戒律。
在这里,我们毋宁说看到了另一个李贽,一个不是“见僧则恶”的李贽,而是一个作为佛教虔诚信徒的李贽。后者在他给其心迩意密的女弟子澹然的信中表露无遗。在这封信中,他不仅告诉澹然“参禅事大”,“回湖唯有主张净土,督课西方公案”,324而且一反其所谓的“何必龙湖而后可死,认定龙湖以为冢舍也”这一说法,宣称“湖上即我归成之地,子子孙孙道场是依,未可谓龙湖蕞尔之地非西方极乐净土矣”,325龙湖这一远离尘世的“蕞尔之地”,竟成为“西方极乐净土”,竟成为他心目中的“子子孙孙是依”的道场,乃至其生命的“归成之地”。
那么,到底是佛教中的什么东西使李贽对佛教是如此的心醉神迷,乐此不疲,使李贽有家弃家、有发落发地成为佛门的虔诚弟子,使李贽最终出尔反尔地竟然把龙湖视为其生命的皈依之地?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就不仅要回到李贽所生活的特定的时代语境,以及这种语境为李贽所引发的生命意义的危机,而且还要回到李贽所理解的佛教,以及这种为其所理解的佛教中的犹如精神解药般的真正胜义。关于后者,就不能不涉及李贽为我们所推出的所谓“三教异同论”理论。
在《初潭集》里,李贽写道:“儒释道之学一也,以其初皆期于闻道也。必闻道然后可以死,故曰:‘朝闻道,夕死可矣。’非闻道则未可以死,故又曰:‘吾以汝为死矣。’惟志在闻道,故其视富贵若浮云,弃天下如敝屣然也。然曰浮云,直轻之耳,曰敝屣,直贱之耳,未以为害也。若夫道人,则视富贵如粪秽,视有天下若枷锁,唯恐其去之不速矣。然粪秽,臭也,枷锁,累也,犹未甚害也。乃释子则又甚矣。彼其视富贵若虎豹之在陷阱,鱼鸟之入网罗,活人之赴汤火然:求死不得,求生不得,一如是甚也。此儒释道之所以异也,然其期于闻道以出世一也。盖必出世,然后可以免富贵之苦也”。326
在这段著名的论述中,李贽实际上为我们道出了两层意思。首先,他告诉我们什么是儒释道三者之同。这种同,就是他所谓的“以其初皆期于闻道”。而这种所闻的“道”并非是道学家心目中的那种异己于人、外在于人的“天理”之“道”,而是“吾以汝为死矣”、作为存在主义式的“向死而在”的“道”,作为人生命的终极目的、终极归宿的至为切身切己之“道”。此即李贽所谓的“凡为学者皆为穷究自己生命根因,探讨自家性命下落”,327而真诚信奉道者,都是他所谓的“爱性命之极也”的人。328也正是由于视道为人生命的终极目的、终极归宿,由于信奉道者为“爱性命之极”,这就决定了对道的追求可以使人对世间的一切置若罔闻,可以使人“视富贵若浮云,弃天下如敝履”,也即决定了期于“闻道”必然志在“出世”。此即李贽所谓的儒释道三者“其期于闻道以出世一也”。
其次,除了这一三者之同外,李贽还告诉了我们什么是儒释道三者之异。这种异只是表现为三者在“期于闻道以出世”的程度上不同。儒家视富贵若浮云,弃天下如敝履,仅仅是对世间的一切“轻之”“贱之”。而“未以为害也”;道家视富贵如粪秽,视有天下若枷锁,亦仅仅是以世间一切为“臭”、为“累”,而“犹未甚害也”。与之不同,唯有释家视富贵若虎豹之在陷阱,鸟鱼之入网罗,活人之赴汤火,则把世间的一切直目为是使人“求死不得,求生不得”的东西,欲逃之犹恐不及,它实际上体现了我们人类“期于闻道以出世”这一人生追求之极致。无怪乎李贽称佛乃是“世间一个极拙极痴人”,说他“舍此富贵好日子不会受用,而乃十二年雪山,一麻一麦,坐令乌鹊巢其顶”,想必其间必有一“世间无一物可比尚”的“至富至贵”,以使他“竭尽此生性命以图之”。329也无怪乎李贽在对比儒释道三家后得出,虽然历史上三教归一,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已今非昔比,今日真正能够做到求道并出世的人,却则非死心塌地的释家的“和尚”而莫属。330
因此,也正是在这里,我们为李贽找到其皈依佛门的最终答案。也就是说,李贽之皈依佛门,与其说是出于一种一时的权宜之计,不如说是出于一种深思熟虑的人生之举,也即出于李贽所自供的“虽孤苦亦自甘之”的“为道日急”。331固然,作为泰州学派的忠实传人,李贽所坚持的“身道”之“身”是一种“食色,性也”、一种“饮食男女人之大欲”之“身”,然而,作为大易精神的真正继承者,这并不妨碍他所坚持的“身道”之“身”,同时又为一种“万化根于身”的宇宙大化之“身”。故李贽所理解的“身”无疑具有一身两体的性质,其既是有限的,又是无限的;既具有生物特质。又不失超生物的品性。这同时也决定了,李贽所追求的“身道”既为世间法,又为出世间法;既为生灭法,又为不生灭法,以至于世间托于出世间,生灭托于不生灭。这是“身道”的究极意义,唯此才有了儒家所谓的上下与天地同流的“真快活”,唯此才有了佛家所谓的一破“俱生我执”的“大自在”。它为李贽所独悟,并为今人梁漱溟先生所畅揭其义,却惜乎不仅为执于肉身的饮食之人,也为只知“吾患有身”“有身是苦”的那些陋释失之交臂了。
故李贽所理解的佛教,实际上乃是一种“存在主义”意义上的宗教。这种佛教虽讲“照见五蕴皆空”,却同时“不住涅粲”地惟身是依;这种佛教虽讲“超越生死海”,却同时“不舍众生”地使人“爱性命之极”。也正是这种佛教,使人们在其所强调的所谓“金刚不坏之性”中,重新发现了儒家所强调的所谓“至诚无息之理”,使我们这个被外人目为“只有肉体而没有灵魂”的民族,恰恰在自己身上找到了其自己精神的皈依,使中华帝国这一长期浸淫于世俗化生活中的无神论的国度,像其他有神论民族一样地衣被神恩的沐浴。也正是这种佛教,在我们帝国日渐沦为“动物王国”之际,不仅以所向披靡之势迅速风靡整个中华大地,使其子民的坟墓成为佛国的发祥地,使其土地到处佛寺林立,乃至使佛教在中国得以有“一观而必有十庙”这一空前的礼遇,而且也乘虚而入地满足了国人嗷嗷待哺的灵魂,使上至梁武帝这样的皇帝下至凡夫俗子,无不对之趋之若鹜、望风顶礼。而李贽之皈依佛门之举,不过仅仅是其中的一例。
因此,也只有在这种“存在主义”的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李贽所皈依的佛到底是什么,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李贽宣称“夫所谓仙佛与儒,皆其名耳。孔子知人之好名也,故以名教诱之;大雄氏知人之怕死也,故以死惧之;老氏知人之贪生也,故以长生引之。皆不得已权立名色以化诱后人,非真实也”,332在其心目中的佛并非是“唯实论”的佛,而仅仅是巧立名目和方便说法的“唯名论”的佛;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李贽在其芝佛院为佛塑像时,既反对众僧为佛用活鸡血点睛,又反对为佛“安五脏”,乃至为佛留有“后门”,而是提出“有心则灵”,提出“是佛菩萨之腹脏常在吾也”,333坚持佛之心即我心,佛之身即我身这一“即心成佛”“即身成佛”之说;我们也才能最终理解为什么不仅黄宗羲在其《明儒学案》里,会对李贽之流的泰州学派遽下“益启瞿昙之秘而归之师,盖跻阳明而为禅”这一归佛趋禅的断语,而且李贽本人也旗帜鲜明地宣布:“真圣人必敬佛,真圣人之徒必不辟佛”,334并不打自招地供认:“果能知三身即一身,则知三世即一时,我与佛说总无二矣。”335
然而,这一切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断然地得出,李贽乃是真正的佛教信徒,乃是真正的佛门弟子。这是因为,李贽固然对佛教不无顶礼,其思想固然与佛教思想心心相契,但若进一步深究,我们却依然可以发现二者之间同中有异,发现二者之间的不无抵牾之处。这种差异和抵牾之处主要表现为,虽然李贽一反“媚俗”而走向“脱俗”,一反“媚世”而走向“愤世”,而对佛教的“出世”之旨给予了高度的认可,同时,却由于其思想与中国身道传统千丝万缕的联系,由于中华民族的“人世情结”业已内化为其心灵深处的“集体无意识”,这使李贽无论在其思想上还是在其行为上,实际上都始终在“出世”与“入世”之间徘徊游移,都实际上始终与佛教的遗事物、弃人伦这一不无决绝的“出世”的人生态度保持距离;这使李贽自称“和尚”实为心出家而身在家的“居士”,口倡“佛学”实宗中国式的“禅学”,而使其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准佛教”的信仰者。
故我们看到,一方面,李贽大讲“儒释道一也”的“出世”,另一方面,又坚持“入世”乃为不可逃遁的人生之旨。此即李贽所谓的“以舍‘人间世’,无学问也”,336此即李贽所谓的“经世之外,宁别有出世之方乎”?337一方面,李贽极言“五蕴皆空”的“空”,另一方面,又坚持“空即是色,更有何空”。338故他不仅告诉女弟子明因“真空既能生万法,则真空亦自能生罪福矣”,339而把那种不能生万有的空,称作是一种“其顽然如一物然也”的所谓“顽空”,340并且面对“老先生肚里是何等空空洞洞”这一对他的恭维,疾声对曰:“我方才吃了两碗粥,有什么空空洞洞”?341一方面,李贽以“有家真是累”而肯定了“出家”,另一方面,又以“家家自有夜明珠”而“为语贫儿休外走”。342故他除了提出“念佛时但去念佛,欲见慈母时但去见慈母,不必矫情,不必逆性,不必昧心,不必抑志,直心而动,是为真佛”外,343还告诉人们:“果生死道念真切,在家方便,尤胜出家万倍。……则在家修行,不更方便乎?”344一方面,李贽不无笃奉佛的“生死原是超的”这一“超生死”之旨,另一方面,又同时以“你要出生死,便入生死了”为人生信念。345故他既一反众人所谓的佛氏戒贪之说,而视佛为贪生怕死之“真大贪者”,346又宣称“苟有佛,即便有魔,即便有生有死矣,又安得谓之父母未生前乎”?347而把一切所谓的“超生度死”之说目为不经之谈。
李贽在思想认识上是如此,其在人生践履上亦不例外。他的一生就是既出世又人世的一生,就是一种所谓的“俗不俗,僧不僧”的一生。一方面,正如他自称那样,其“任性自是,遗弃事物,好静恶嚣,尤真妖怪之物,只宜居山,不当入城近市者”,348一种天性使然,使他那样义无反顾、万牛莫挽地遁入空门,另一方面,又正如其自供的那样,他对人间世是那样的一往情深,那样的难以割舍,以至于其行为“绝未曾自弃于人伦之外”。349后者表现为,这位“卓吾和尚”他“不持斋素而事宰杀,不处山林而游朝市,不潜心内典而著外书”,350虽身处佛门却嗜肉吃荤,虽名为山人却入城近市,虽宗禅默却著述颇丰,表现为李贽本人“年来鬓发随刀落,欲脱尘劳却惹尘”,351虽手起刀落而使自己“有首无发”,却永远不能了断自己的儿女之情、朋友之情、家国之情,不能了断自己心中剪不断、理还乱的纷纷俗世红尘。除此之外,它还尤其表现为,比起那些整天高谈之于庸言庸行“须臾不可离”、高谈“明于庶物,察乎人伦”的道学家们,在人世的问题上,他是那样的更为认真,认真得行不掩言,认真得不会韬光养晦、不会退藏于密,以至于正是这种认真,以其涉世太深,而最终难以自拔地招致了杀身之祸的厄运。
中外学术比较大师梁漱溟先生,在谈到儒佛之异时曾指出,它除了表现为一为“卓然超于俱生我执”,一为“破除俱生我执”,也即一为相对的出世,一为绝对的出世之外,还与之相关地表现为,“佛家期于‘成佛’,而儒家期于‘成己’,亦曰‘成已、成物’,亦即后世俗语所云‘做人’”。他并且指出,“此即儒家根本不同于佛家之所在。世之谈学术者,其必于此分辨之,庶几可得其要领”。352我们看到,也正是在梁公为我们所点出的“成己”抑或“成佛”这一问题上,再次彰显出了李贽之学与佛家之学的区别,并为我们表明了李贽实际上并非真正的佛教信徒,并非真正的佛门弟子,表明了所谓其“皈依佛门”之说可以休矣。
这就把我们引向了李贽旗帜鲜明地推出的“佛不远人”之说。在这方面,他不仅明确宣布“堂堂大道,何神之有”?353对种种作为“绝对他者”的佛给予去魅,而且提出“既成人也,又何佛不成,而更待他日乎?天下宁有人外之佛,佛外之人乎”?354提出“菩萨岂异人哉,但能一观照之焉耳。人人皆菩萨而不自见也,故言菩萨则人人一矣,无圣愚也”,355提出“盖人人各具有是大圆镜智,所谓我之明德是也”,356提出“尽大地众生无有不是佛者”,357以及提出“今之所谓能事人者,事势也,非事人也。真能事人,则自能事鬼矣。故唯大圣人为能事鬼,则大圣人能真事人故也”。358在这里,传统儒家的“道不远人”一变为李贽的“佛不远人”;在这里,传统儒家的“人皆可以为尧舜”演化为“众生无有不是佛”;在这里,佛已经不再是异己于人的彼岸的“绝对的他者”,而成为每一个人性中自有自足的东西。只要我们不自暴自弃,只要我们善于挖掘和发现自己的真实的自我,我们就可以在自己当下即此的人性中找到无比神圣的佛性,我们就可以在践履“为己之学”道路上步入那作为极乐世界的佛的王国。无怪乎李贽宣称只要人“魂灵犹在”,即此“便是西方净土,极乐世界,更无别有西方世界也”;359也无怪乎李贽认定“释氏因果之说,即儒者感应之说”,360因为之所以“获罪于天,无所祷也”,恰恰在于这宗罪归根结底是人之罪,恰恰在于“天作孽,犹可违”,而“人作孽,不可活”,正如存在主义所说的那样,人的命运要由自己来承担和负责。
这样,对于李贽来说,其所宗的佛学与其说是所谓的“佛学”,不如说实际上不过是所谓的“人学”。显然,这种“人学”之“人”,既非那种“阉然媚于世”的逐世混俗的“俗人”,也非那种完全遁入空门而不食人间烟火的“山人”,而是一种既入世又出世之人,一种“身在局中,心在局外”之人,一种“大隐隐于世”的作为“城市隐者”之人。这种人,“市隐何妨道,禅栖不废诗”,虽身处闹市却并无碍于其对形上之道的执着,虽栖居寺庙中却不放弃自己诗意人生的追求;这种人,从容中道于“人之大欲”与“不见可欲”之间,以至于他可以真正做到“发而中节”、可以真正做到“欲而不贪”;这种人,其来到人间并非仅仅为来世做出铺垫和准备,而是他的来世就在此世之中,他生命的瞬间也即其生命的永恒;这种人,他已不再“骑驴觅驴”地别求所谓神性,而是“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其苦苦寻觅的神性本身就存在于他自己的人性之中。
也正是在这里——在这种既新奇又熟识的人性理解里,李贽如醒醉觉梦般地发现,自己又重新回归了中国古代那天人合一的“人文主义”的传统,发现其跋涉不已、尽其曲折所探寻的人生皈依,到头来依然再蹈故袭地以儒学为其不二法门,以儒教为其最高信奉,尽管他一度对孔子是那样出言不逊地大不敬,尽管他以对所谓“酸儒”“腐儒”“迂儒”“鄙儒”“俗儒”“名儒”的力辟,素被时人目为对传统儒学一扫而空的“反儒英雄”。


 张再林
张再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