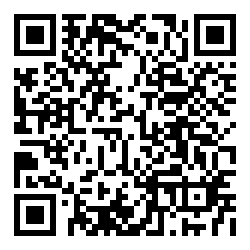“重行”无疑是中国伦理学之为中国式伦理学、中国伦理学之区别于西方伦理学的又一极其显著的特征。而诚如古人“行不远身,行之本也”(《大戴礼记·曾子十篇》)一语所明喻的那样,其重行的根据与机理亦唯有基于传统伦理学的“根身性”才能得以真正的解读和说明。易言之,强调身体必然要强调行为,正如强调意识必然要强调知识:既然中国伦理学以“尊身”为旨,那么其也必然以“重行”而立宗。故中国伦理学既是一种强调“修身”的身体性学说,同时又不失为一种推崇“修行”的躬行主义的理论。
对于古人来说,正如其古汉语所示,“身”字与“生”字异名同谓,“生”被视为是“身”的代称。又古人所谓的“生”乃为“天人合一”之“生”:“尽人道者,动以顺生之几”(王夫之《周易外传·无妄》),意即“生”就天而言为“生”,就人而言为“行”。故古汉语中“身”字即“躬”字,而后者同时兼有“亲身”和“躬行”二义。这样,古人的“身”、“行”合一,“身体”即为“力行”之旨由此就揭橥而出。而身体作为道德的载体又意味着身体行为与道德行为须臾不可分离。故我们看到,古人不仅以“履”训“礼”、以“行”训“礼”,一如《说文》中“礼,履也”,《荀子·大略》中“夫行也者,行礼之谓也”所云;同时古人还以“行”训“德”、以“操”训“德”,所谓“德行”、“品行”、“行谊”、“行状”,以及所谓“操守”、“操行”、“操介”、“操履”、“情操”,适足形容之。
因此,与西方传统坚持“美德即知识”、“恶行即无知”并最终流于“唯心主义”的伦理学不同,不是知识的认识而是行为的践履、不是“以心控身”而是“身体力行”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古代伦理学的中心内容。早在古《尚书》中就有“非知之艰,行之惟艰”(《说命中》)之说,为我们首揭出古人“重行”之旨。尔后,在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学说里该重行之旨又被得以进一步推崇。孔孟不独教人皈依于所谓的“敏行”和
“践行”,还诚如顾炎武所云,在他们的著作中“性命与天道”为其所“罕言”,而“出处,去就,辞受,取与之辨”却为其所“恒言”。接着,为汉人所推出的《礼记》一书代表了古人对周礼的又一次文化复兴,旨在通过整理“国故”重归去今已远的古代行为伦理的传统。人们看到,在中国历史上,这一传统虽随着后来的魏晋玄学、隋唐佛学以及宋明理学的勃起而渐趋消退,然在明清之际其又如初阳朗照般地再次得以中兴。薛瑄所谓“验于身心,体而行之”、王阳明所谓“一念发动处便是行”,王艮所谓“即事是学,即事是道”、刘宗周所谓“本体即在功夫中”、顾炎武所谓“经世致用”,如此等等恰足为其表征。众所周知,在明清众多思想家中,鼓倡行为伦理最不遗余力的当属被誉为“先生之力行为今世第一人”的清代巨儒颜元。他把皓首穷经斥为“率古今之文字,食天下之神智”的“吞砒”之举,把种种心性之学视作“镜花水月”、“望梅画饼”的“泡影学问”,并释学习之“习”字为“如鸟数飞以演翅”,训格物之“格”字为“手格其物”、“犯手实作其事”,提出“身实学之,身实习之”,“重之以体验,使可见之施行”,独尊以“三事”、“六府”、“六德”、“六行”、“六艺”为内容的尧舜周孔之道。这一切,不仅是对业已流于“心口悬空之道”的宋明理学的颠覆性的批判,而且同时也是在否定之否定的历史辩证法的鞭策下,对中国古代行将沦胥以亡的躬行主义伦理这一所谓“实学”、“正学”的再次昭揭。
必须强调指出的是,既然古人所推崇的行为是一种伦理行为,那么这种行为实际上就完全不能基于主客关系维度加以诠释,而唯有依据主体间关系维度才能得以理解。或借用哈贝马斯的术语,该行为不是一种“工具”意义上的行为,而是一种“交往”意义上的行为。因此,该行为既与西方思辨哲学中的立足于人对自然的征服、人之对象化的“实践”活动的行为宗旨有别,又与西方科学中作为生物机体之于生物环境的“刺激—反应”活动的行为相距甚远。它乃是身、行一如地使根身中潜在的“一体之仁”得以真正实现的“践形”,乃是身、生不二地从我的一己之身向族类的社会身的不断的生成。
一旦伦理行为被视为是族类生命的生成过程,那么这不仅意味着该传统伦理行为乃为一种发端于男女夫妇的我与你之间的对话,而且意味着该对话以一种历时性的方式而非共时性的方式展开和发生。而这一切,最终使一种语用论的“动态的互文主义”的伦理行为,也即一种基于所谓“时”的伦理行为成为真正可能。故《礼记》谓“礼,时为大”(《礼记·礼器》),《易》谓“与时偕行”(《易经·乾》),《诗》谓“物其有矣,唯其时矣”(《荀子·不苟》),而郭店竹简亦有“穷达以时”之论。同时,也正是从这一唯时主义的伦理行为出发,才使古人坚持“义者宜也”,不是以必然的“必”而是以适宜的“宜”释“礼义”之“义”,才使古人不仅主张人的伦理行为应该“因时制宜”,而且亦“时位相关”地强调人的伦理行为应“因地制宜”。
明乎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古代伦理实质上乃是一种极其典型的情景式的、交谈式的伦理。人们从孔子这一“圣之时者”身上看到的东西足以为证之。孔子虽被人仰视但却从来不以权威者自居,他只谦逊地承认自己是一位“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老师,他的工作仅仅是与弟子你问我答地相互切磋,他很少遽下断语甚至坦言自己言语有失之处。此外,他对弟子的教育总是因人设教、因机设语而从中寓含着深刻的启发,与他相处你会感到一团和气,与他交谈会使你如沐春风如被时雨。所有这一切,恰与苏格拉底的貌似对话而实为“争辩”、“较真”的伦理,更与基督耶稣宣称自己是“上帝之子”、宣称“我是王”、“要听我的话”的那种坚持“非此即彼”的权威式的戒命式的伦理形成鲜明的对比。
明乎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古代伦理已不失为一种“消解伦理”或“后伦理”的伦理。易言之,在中国古代伦理学里,伦理已失去其一成不变的规定而成为一种不落方所的所谓的“无体之礼”(《礼记·孔子闲居》)。故孔子提出“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孟子提出“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孟子·公孙丑上》),荀子提出“善为诗者不说,善为易者不占,善为礼者不相” (《荀子·大略》),乃至王阳明最终提出“良知即是易”(《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在其学说里,伦理与“不可为典要,惟变所适”的“易理”已完全成为异名同谓的东西。因此,“经非权则泥”(柳宗元语),在中国古代伦理学里,其伦理行为之“经”与伦理行为之“权”已相为表里地联系在一起。正如郝大维、安乐哲所说,古人行礼如同习字,其既遵循一定规范又为个人自由创造留有余地。故对于古人来说,“嫂溺,则援之以手”并非与“男女授受不亲”之礼相抵牾,“汤放桀、武王伐纣”并不意味着对“臣事君以忠”的古训之否定,甚至“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这一“为亲者讳”都被视为“直在其中”的道德品质为孔子加以礼赞和称颂。
因此,从这种时的伦理行为、这种“无体之礼”中,古人毋宁说为我们推出了一种不无生动不无圆融的人类伦理的最高化境。在这一化境中,既无道德的唯意志论的安身之所,也没有道德的决定论的委命之地;在这一化境中,不仅伦理中的自律与他律的对立涣然冰释,而且伦理中的语义和语用二者也已不再判然有别。此即古人的“应感而发”、“见机而作”的“时中”,也即古人的语义之诚实与语用之真诚相统一的“诚”,也即孔子自述中所明揭的作为人生命之巅峰的“从心所欲不逾矩”。它向我们表明,古人的“立于礼”已礼艺相通地“游于艺”,在中国古代伦理学里,其对之诚惶诚恐而不敢越雷池一步的作为道德禁忌的伦理的“礼”,最终竟如《说文》所谓“美与善同意”、孔子所谓“尽善尽美”所示,与优美的、从容自如的和作为“无法之法”的艺术的“艺”别无二致而滚作一处了。
《易经》“履”卦卦辞曰:“履虎尾,不咥人,亨”。从这一极其夸张而富于想象的隐喻里,不正是为我们活现出古代伦理行为(“履”)的践行者所身怀的“游于艺”的绝技吗?


 匿名
匿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