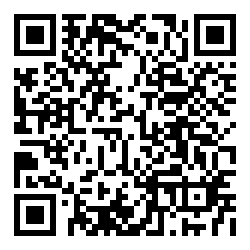德鲁克认为,20世纪有四个部门保持了发展势头,它们分别是:政府、卫生保健、教育和休闲147。这四个部门正是知识型组织最为集中的部门,也是管理问题集中的部门。要提高知识型组织的生产率必须解决以下几个问题,影响知识工作者生产率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如何衡量和提高知识工作者的生产率?谁是知识型组织的管理者?知识工作者将以何种形式组织起来?这几个问题不过是管理的几个基本问题在知识社会的表述形式,但这些问题还远没有答案。比如说,在中国目前投诉最多的行业是医院和学校,只要看一看今天医院和学校管理的混乱局面,就不难理解管理知识型组织的困难。
对知识工作者的管理是知识社会的中心任务,其核心目标是在提高知识和知识工作者的生产率的基础上,提高组织资源的综合生产率。组织变革的根本目的仍然是为了提高知识工作者的生产率。在德鲁克当时看来,还没有人真正考察过从事科研的白领工作的生产率,大学、医院和教会是最大的知识工人雇主当中的三种,其生产率是令人沮丧的148。
要想提高知识工作生产率首先必须能够衡量它,而要想衡量知识工作的生产率首先必须要理解这种工作的经济性质。在工业化的过程中,人们花费了100多年的时间才学会了衡量制造业的生产率。但是对于知识工作而言,人们现在甚至还不知道要衡量的对象究竟是什么。德鲁克指出,知识工作具有与体力劳动完全不同的特点:就体力劳动而言,尽管边际替代率会越来越高,但体力劳动和资本投入是可以相互替代的。这是古典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设,制造业的自动化证明了这一点。然而,知识工作与体力劳动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专业工作者不可能由资本投入所替代。恰好相反,一个组织中资本投入越多其需要的知识工作者也越多。
最有力的证明是医院和学校。以医院为例,如果医院加大对医疗设备的投资,就必须为这些新设备配备训练有素的操作和维护人员,从而带来更多新的高收入工作。学校教育的生产率主要取决于教授的生产率,提高教授的生产率的途径之一就是让教授专心一意地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事实上,在许多知识型组织中,这一看起来显而易见的道理却普遍被忽略了。在学校里,教授的主要精力并没有全部用于教学和研究,许多教授花费了相当多的时间来填写各种表格,应付各种检查。类似的情形在知识型组织里随处可见,造成的生产率损失难以估量。
这是管理领域的一个新难题,尽管德鲁克在1986年出版的论文集《管理的前沿》中讨论了测定知识工作者的劳动生产率的方法,但总的来说这仍然是一个崭新的领域。知识工作者以专业知识为生产工具,而知识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迅速老化,因此知识工作者的生产率取决于其更新知识尤其是有效运用知识的能力。学习和掌握知识已属不易,但知识本身并没有价值,只有在运且中知识的价值才能得到体现。
德鲁克认为,知识工作者必须学会将专业知识和其他广泛的知识以及人类的经验相连接,否则是不能产生绩效的。以保险业为例,保险新品种的设计主要是依靠保险精算师。然而,近年来大学培养的许多精算师却不能胜任新产品设计工作。这些年轻人在专业知识方面是很不错的,但是一个称职的更不用说优秀的精算师必须具备三个方面的知识:精算方面的专业知识占1/3,社会生活常识占1/3,商业知识占1/3。学习这三个方面的知识已经是很大的挑战,而要想成为一个优秀的精算师,还必须将这三个方面的知识连接起来,然后将融合为一体的知识运用于自己的工作中。如果没有这种融会贯通的能力,我们将只拥有许多专业知识而已。可见,对受过教育的人而言,他们的极大挑战便是将自己所知的知识和技能运用于工作。
谁是知识型组织中的管理者呢?一般地说,管理者就是对下属工作负责的人,然而,知识工作者往往没有下属。因此,德鲁克提出,管理者不再是对下属的工作负责的人或对他人的业绩负责的人,而是对知识的应用和知识的绩效负责的人。德鲁克甚至认为管理者(Manager)一词隐含着控制和权威的含义而不再适用于对知识工作者的管理,他更倾向于使用比较中性的执行官(Executive)来代替。由于组织中的管理人员不再掌握有效的决策和控制的充分信息,这些管理人员将不再是决策的制定者,他们的角色转变为教练和顾问。同时,德鲁克再次强调,知识工作者在依靠知识的力量摆脱了外在监督和控制之后,个人必须负起自我发展和自我定位的责任149。不过,仅仅指出个人必须负起自我发展和自我定位的责任是不够的,重要的是如何做到自我发展和自我指导,德鲁克在《卓有成效的管理者》一书中对这个问题提供了很好的建议150,在《21世纪的管理挑战》中他重申了这些观点。
因为知识是专业化的知识,而专业知识必须结合在一起才能创造绩效,这意味着专业人员必须通过一定的方式组织起来。专业人员占主体的组织面临两个难题:一是专业知识与组织绩效之间的矛盾:二是知识工作者与其他员工的合作问题。
对于第一个问题,主要困难在于现有组织在衡量知识工作者的业绩时采用了双重标准。传统的蓝领工人只需完成组织安排的工作任务就达到了目标,而专业人员要同时为两个目标服务:一方面,专业人士的工作首先必须符合专业要求的标准;另一方面,作为组织的一员专业人员必须完成组织赋予的任务。追求双重目标的结果使得许多专业型组织成了所谓的“双头怪物”——专业人员必须同时对相互冲突的双重标准负责。其次,这些专业人员的知识是如此专门化,以至于组织中无人能够有效地领导他们。比如,每个医院只需要少数几个X光仪器操作师,大多数企业只需少数几个计算机系统维护人员,许多小企业甚至只需要一个兼职的财务管理人员。
一个组织往往需要各种不同类型专业人员的服务,各个专业的人数又只需要少数几个,组织中的管理人员如何能够有效领导和激励这些人呢?近年来,欧美国家出现的所谓专业雇员组织(Professional Employee Organization,简称PEO)是解决这些问题一种成功尝试151。这种PEO组织由同一领域的专业人员组成,PEO的雇员只需对专业目标负责,由PEO组织对其雇员按专业要求进行专业训练和评价。PEO将专业雇员介绍给需要专业服务的组织,专业人员与这些组织之间形成临时雇佣关系。在雇佣期间,专业人员必须完成雇主分配的任务,即对组织目标负责。这种新型组织将专业人员与其他雇员分离开来,既避免了双重目标困境,又使专业人员得到有效管理。
如前所述,21世纪发展最快的部门是知识型组织最为集中的地方,医院和学校是这类组织的典型代表。事实上,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绝大部分医院与学校都是属于非营利性组织(在我国既有事业单位也有社会组织)。从德鲁克将非营利组织看作工厂社区的替代物来看,他所指的非营利组织主要是提供社区服务的机构,关于这类组织的管理问题留待下文讨论。这里所讨论的知识型组织主要是指第三产业或服务产业(包括金融、科技、教育、医疗卫生、文化娱乐、体育、休闲等行业)中知识和专业人才密集的组织。
今天,组织理论是管理学领域发展最快的领域,新名词新理论层出不穷。传统组织被称为科层制组织、金字塔组织、机械型组织、封闭型组织,信息时代的组织则被称为扁平型组织、蜂窝型组织、生态型组织、学习型组织、虚拟组织等等。不管这些组织概念名称如何,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今天的组织已经不同于传统的组织。从某种程度上讲,知识型组织是以信息为主要生产资源的组织。传统的企业组织模仿军队的体制,以信息为主的组织则更类似于医院或交响乐团,而非典型的制造企业152。某种意义上说,知识型组织的管理比交响乐团还要困难得多。在交响乐团中,乐谱已经交给演奏者和指挥。而在企业中,乐谱是在演奏的过程中,边演奏边写成的。为了知道乐谱是什么,在以信息为基础的组织中,每个人都必须通过实现一致赞同、人人清楚明了的目标来管理。因此,目标管理及自主管理必然是以信息为基础的组织的一体化原则153。
在知识型组织中,德鲁克尤其关注高等教育的管理变革。每一种早期的高等教育制度——中国的、美国的、日本的——都把学校视为社会流动的催化剂,通过这种流动,才华横溢奋发有为的“下等阶级”人士可以进入社会上层和获得社会地位154。在早期,人们在大学毕业之后,学业就完成了,在大学阶段学过的知识几乎可以伴随整个职业生涯,因此,一旦大学毕业,人们就成为“受过教育的人”。今天,由于知识的迅速老化,受教育成为持续终身的事情。
德鲁克提出了教育在知识社会新现实中负有的新的责任:第一,教育要关注社会目标,知识社会面临的危险是,有知识的野蛮人将充斥社会。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学校有必要使学生为谋生做好准备。第二,教育必须是一个开放的体系。第三,树立终身教育的观念,注重继续教育。第四,教育将不再局限在学校之内,每个工作单位都要成为学校。第五,教育的社会责任在于防止“精英管理”蜕化为“富豪统治”155。从教育的责任出发,德鲁克对信息时代大学的学科与院系的设置,教师的管理及其道德问题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今天的大学其是以学科和院系为基本构成单元组织起来的,这种组织模式已经变得过时。跨学科研究的兴起与学科之间的融合,向知识领域的每一种分界线发起了挑战。“生物学与化学之间的分界线,生理学与心理学之间的旧分界线,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旧分界线,社会学与行为科学之间的分界线,逻辑、数学、统计学和语言学彼此之间的旧分界线,都正在日益变得没有意义。每一种旧的划界、旧的学科和旧的学院都将变得过时,并成为学习和理解的障碍。”156
造成这种情形的根本原因在于知识与行动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彻底的变化。今天的大学基本上是知识本身的门类体系来划分院系与学科的,这种划分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知识与行动之间没有联系,知识与应用可以相互分离。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大学的院系、学位与专业,乃至整个高等教育都是根据知识本身的表面逻辑组织起来的。通俗地说,这种组织逻辑是“产品导向”或“生产导向”而不是“市场导向”或“应用导向”。在企业已经普遍认识到“顾客即企业”之时,大学的组织还在沿袭19世纪的组织逻辑。
现在,知识从目的转变为一种生产资源,转变为一种促进创造价值的手段,成为现代生活的核心资源,知识因此与行动和应用紧密相连,大学在传统的教学和研究功能之外加上了社会服务功能。这意味着大学的组织在考虑知识本身的分工之外,要考虑其在应用领域的融合,还要考虑社会对学生的需要。这意味着管理大学成为最具有挑战性、最困难然而也是最重要的任务。
在具体政策和管理制度方面,德鲁克也对西方大学提出了批评和建议。他主张发展大众教育,反对偏重精英教育;主张教育资源的均衡分配,反对教育资源过渡集中于少数名校;主张社会平等对待各个学校的毕业生,反对文凭歧视;主张充分竞争机制,反对教师终身雇佣制。
在教育的社会责任方面,德鲁克主张有知识的人要在政治决策中发挥影响,要对教育的成果负责。指出“有知识的人要为教育的业绩承担责任。责备学生学得不好,不再是可以接受的理由。学生学得不好,那是学校的失败。学生不想学习,那是学校的耻辱,也是学校和教师应该受到谴责的理由。”157我们今天为之争论不休的学术道德问题,德鲁克少有提及,显然,这是社会责任的题中应有之意。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几十年当中,美国建立了许多庞大无比的学校。德鲁克指出,这就是今天教育沉疴的祸首。现在的学校纷纷走向多元化与非中心化,所谓的磁铁学校(指美国以种族融合为目的而创办的学校)就是一例158。


 张远凤
张远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