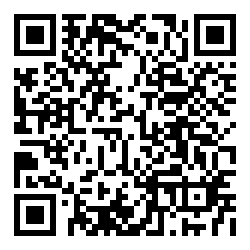认识是行为的起点。管理学,作为一种有关人的社会行为的方式及规律的学说,其实是以人认识世界的一定的认识论模式为其哲学滥觞的。同时,也正是从不同的认识论模式出发,形成了风格迥异的中西各自的管理思想。
众所周知,长期以来,西方的认识论是基于西方现代现象学学者所刻意揭露和批判的“现象”与“本体”二分对立这一先入之见之上的。这一认识论模式假定,人只能把握事物的“现象”,而该“现象”背后的“本体”则属人的认识鞭长莫及的“物自体”。由此便形成了与先验本体无缘的、以外在经验事实作为研究对象的西方人所谓的“经验科学”,而把这种经验科学推及到人类社会,就形成了西方人的以经验主义为其哲学特征的所谓“行为科学”,即“管理学”的学科。
经验主义必然导向价值取向上的功利主义。这种经验主义的“管理学”认为,正如自然对象之于人仅为人的一种实用之物一样,人的社会行为之践履亦完全服务于人的一种功用所需,故追求所谓“效率”成为这种管理学的唯一目的。因此,管理学是一种纯粹的“应用性学科”,对人类行为的管理不过是实现某种外在于人自身的管理目标的一种手段和工具,这就导致了“经由他人完成事务”这一西方实用主义的管理学主旨的提出。
这其实是一种“有用无体”的管理学说。它强调人的行为的“效率”,但却不问人的行为本身的“意义”;它强调人的行为是一种外在的“手段”,但却无视人的行为亦有其自身内在的“目的”。因此,西方的管理学说是建立在“体”、“用”分离、见“用”忘“体”的基础之上的,它是一种“无根的管理学”。这种唯用主义的管理学在西方近代管理学之父泰罗的管理学说里曾得以最充分的体现。在泰罗的学说里,管理活动的宗旨仅在于提高劳动生产率,作为被管理者的人毋宁已成为为获取更多利润而高效运转的一架无灵魂的机器,从中人已经完全遗失和辨认不出“自己”了。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则不然。如果说西方管理思想是基于本体与现象二分这一思想的产物的话,那么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则源自其现象即本体这一“彻底经验主义”思想。在中国古人看来,本体与现象并非对立的二元,而是一种“显微无间”、“上学上达”的一元整体。在这一整体里,现象并非是与本体无缘的东西,而是本体本身的显现和生成;本体亦并非是现象背后的“物自体”,而是现象本身的潜在形式。因此,本体不是某种实体性的东西,而是“即用显体”,即被看作为一个展开于具体现象之中的功能性过程。由此便形成了中国古人本体与功用合一即“体用不二”的“道”的思想。而“礼,履也”(《说文解字》),把这一“道学”思想运用于人的行为(“履”)领域,则形成了中国古代管理学说中别具一格的“礼治主义”。
与西方那种有用无体的“科学行为”不同,礼是体用为一的人的行为整体。在这一整体里,人的社会行为不是追求某种外在功利目标的单纯手段,而是作为个体生命本身的“性”的表现形式。具体言之,它是“因人之情”的一种活动,是由“亲亲”这一始原亲情向社会、他人领域的辐射的“移情”过程。也即《诗》所谓的“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孟子所谓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样一种“举斯心加诸彼”。在这里,“复礼”即为“复性”,作为人的社会行为的“礼”与个体生命本质的“性”是完全为一的。这样,一方面,礼是用,礼作为人的行为的“经纬蹊径”具有明确的社会管理之功用。即所谓“礼者何也,即事之治也”(《礼记》),“礼之所以正国也”(《荀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孝经》),“明乎郊社之礼,禘尝之义,治国其如示诸掌乎”(《中庸》)。另一方面,礼是体,作为“性”的表现形式“礼反其所自生”地又与宇宙以及人的终极本体的道联系在一起。即所谓“礼者,人道之极也”(《荀子》),“礼也者,反本修古,不忘其初者也(《礼记》),“礼必奉于大一”(《礼记》)。
这是一种从“行为本身”出发的管理学说。对于中国古人来说,管理,已不再是使管理对象服务于某种外在的社会管理目标的一种单纯的“事务”,而成为作为被管理者的人的一种“尽性”与“践形”的过程;管理学,也不再是一种纯技术的“应用科学”,而成为一种具有鲜明价值判断特色的人的生命学说。正是从这一点出发,使中国古代管理学说在人类管理活动中始终坚持、呵护了人自身的意义,避免了实用主义、功利主义所带来的对人类行为自身根据的异化和偏离,以其鲜明的“人本主义”特色与西方“无人称”的管理学说形成尖锐对比。
同时,中国古人坚持管理中“人本”这一“体”的意义并不意味着无视作为手段和方式的“用”的重要性。中国古人不仅在其管理实践中一度建立了和发明了令世人叹为观止的“经礼三百,曲礼三千”这一详尽明备的礼仪用制,而且坚持管理活动中的“体”的意义唯有通过一定的“用”才能使自身意义得以显示和彰明,所谓“礼以器藏”思想的提出就是其明证。因此,在中国古代管理活动中,不同的行为规定是借助于不同的礼数和仪制规定来进行的,管理不啻成为一种“礼以行义”的过程。它使人类的管理活动既坚持目的的价值又强调手段的运用,既坚持“人本”的意义又不流于“唯灵”、“唯识”的空论,从而又与形形色色唯心主义的社会学说的宗旨大相径庭。
这样,在中国古人以礼为其形式的管理活动中,种种被西人视为背反的二律——体与用、目的与手段、内在欲求与外在规范毋宁已实现了其有机的统一,礼的形式已成为一种既有一定形式规定性又与无规定的人的终极实在相关的“有意味的形式”,即审美的形式。古人云,“知乐则几乎礼矣”。我们看到,中国古人的“礼”与“乐”在精神上其实是完全同一的。而这一审美的“人文主义”的礼治思想的提出,无疑为人类的管理学说揭示了一极为深刻的主旨:管理并非是一种以“必然”为其内容的“科学”,而实质是以“自由”为其灵魂的“艺术”。
这就把我们带到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又一主题,即“行为自律”。


 匿名
匿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