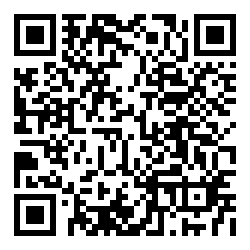中国古代宗教文化之所以具有上述特点,和中国古代的宗教思想有特别关系。中国古代宗教思想本身也具有不同于西方基督宗教神学的特点。
西方的宗教思想是以神为中心建立起来的观念系统,宗教活动如人信仰神,祈求神,认识神,追求神等等,都是人以神为中心进行的活动。中国古代宗教思想的特点是,它也承认神(如殷人的“上帝”、周人的“天”、道教的神仙、佛教的佛等)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承认神有主宰世界的能力,但并不因此就断定人在神面前无能为力,甚至一无是处。中国古代的宗教家并不鼓励、引导大众去探索“神”本身的性质和意义,并根据这些探索成果建立系统的神学思想体系。他们不去证明神的存在,分析神的结构,描述神的性质,他们没有建立起中国古代的神学,甚至没有这样的意图。在他们那里,神的存在、权能等,似乎没有成为问题。比起西方宗教来,中国古代的宗教在神学理论上有朴素性,中国古人的所谓“天命”被孔子、孟子等纳入理性认识的“知天命”和道德实践的“正命”“立命”范围,若人认识实践范围之外的天命,则尽皆承认之、敬畏之,但又“罕言”、“不语”,敬而远之;而死亡问题,则被纳入“未知……焉知……”的框架中,实际上被悬置起来,不进行正面探讨。但在神与人的关系方面,又强调人性与“天”或佛性的内在联系,甚至认为二者是等同的,十分突出人在神面前的地位,体现出宗教思想的人文特色。儒家的人可以成圣,道教的人可以修炼成仙贤,达到“天人合一”境界,佛教的人则可以修养成佛,达到佛人合一境界。但西方基督宗教的人却决不能修养成神,“天人合一”的说法对他们来说,太理想化了。586
用历史眼光看,中国古代宗教文化的一般特点、中国古代宗教思想特点的形成,都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先秦诸子学、两汉经学、宋明理学、明末清初实学由于在古代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它们在中国古代宗教思想特点的形成过程中,都发挥过重要作用。从思想内容看,中国古代宗教思想的特点和儒家关于“天”与“人”关系的看法,有最为密切的联系。
儒家“天人关系”思想,在占据中国古代宗教思想的主导地位的同时,又深刻地影响着佛教的佛性论、道教的“内丹”说,充分地体现出中国古代宗教思维方式的特点。这个特点,在学术思想方面就表现为,探讨神(“天”或“天命”本身)的神学不发达,而理性地探讨“天”与“人”联系的中介——这个中介,被儒家断定为是人的本性,即“德”性,也被中国佛学断定人人都有的佛性,也被道家道教断定为人人都有的“道”(“玄德”)——的学术思想一直十分发达,连绵不绝。
在儒学思想里,“天”作为人性的来源,比人性的地位高,但儒学探讨的重心在人性,而不在天性。儒学主要的是人学,而不是探讨天性的天学或神学。比如,儒家经典《中庸》明确提出“天之道”这个概念来,努力从“道”的角度,理性地理解“天”。《中庸》还引用这样的诗句描述“天”:“维天之命,於穆不已”,“上天之载,无声无臭”587。这样的“天”,人格色彩很淡薄,只是抽象的、无穷变化的神奇实体罢了。虽然董仲舒一度提出了“天命鬼神”这样人格色彩强的“天”概念,但很快遭到王充元气自然论的驳斥。后来的宋明理学家又不约而同,将儒家的“天”理解为世界的根源和材料(“气”学家所理解的“气”)、根据和性质、规律(理学家理解的“理”)和主体(心学家所理解的“心”),理解为理性可以把握的“道”。儒家天人关系的探讨,终于被拉回到理性探讨的道路上来,定格在理性的人学画面上。
儒家“道”的信仰,对佛教、道教的宗教信仰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即使有人格色彩的各种佛、菩萨等,即使有人格色彩的各种神仙、鬼神等,也只是佛性或“道”的人格化。神就是“道”的人格化,“道”就是神的本质。在世俗的人们看来,神不比“道”高,反而“道”比神更重要,是“道”统一、主宰着这个世界,而不是神灵。与儒家将“天”进行“道”的理性化理解相应,在完成中国化以后的中国佛教思想里,“佛”只是觉悟的人,而不是神,中国佛学思想的核心概念也是人人都有的佛性,而不是佛本身。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佛学也不是神学,而是人学。道家是强调人的自然天性的人学,更不是神学。道教虽然大讲神仙,但所谓神仙,也都是平凡的人得“道”以后所达到的理想境界,这样的境界平凡人都可以修养达到,所以,道教思想也主要的不是神学,而是人学。
在古代中国思想史上,占主导地位的看法是,“道”才是将世界统一起来的唯一者,而不是人格神。即使存在着鬼神,人们依靠自己对“道”的修养,也可以对付。刘向《新序》借用晋文公的口说:“夫神不胜道,而妖亦不胜德,祸、福未发,犹可化也。”所以,现实中有些人“无究理而应天”,是不对的,只要自己在学习中不断提高自己的修养,“应之以德”588就足够了。在儒家学者看来,天、命、性、道、教,以及气、理、心等,是完全统一的,都是“天人合一”的中介环节。王阳明说:“道即是教。”589他这句话,正好揭示出中国古代儒家宗教思想的理性秘密。
中国古代儒家关于“道”的信仰或信念,是古代中国理性信仰的典型代表。在古代儒家学者看来,“道”作为信仰的对象,主要指“气”“理”“心”等理性的思想范畴,修道方法主要是学习、克己等理性的认识、实践方法,修道所达到的与“道”为一的境界,也是现实的人都能够通过理性努力达到的理想人生境界。
在古代中国儒家学者那里,“道”作为理性的思想范畴,主要是指“气”(主要指生命、动力、材料)、“理”(主要指形式、真理、规范)、“心”(主要指精神、主体、自由)。由于“心”的因素,“道”没有很浓的人格色彩,但有一定的人格。比如,“道”有一定的目的性。理学大家朱熹根据《易传·系辞传下》所谓“天地之大德曰生”,和《二程遗书》卷二上所谓“天只是以生为道”的说法,强调“天地之心”的目的性因素,说:“天地以生物为心者也,虽气有阖辟,物有盈虚,而天地之心则亘古亘今,未始有毫厘之间断也。故阳极于外而复生于内,圣人以为于此可以见天地之心焉。盖其复者气也,其所以复者,则有自来矣。向非天地之心生生不息,则阳之极也一绝而不复续矣,尚何以复生于内而为阖辟之无穷乎?”590在朱熹看来,万事万物生生不已,就是“天地之心”的表现,也是“道”目的性的表现;作为世界的目的,“天地之心”当然就是万事万物生生不已的永恒动力之一。同时,因为“天地之心”的存在,作为“天命”或命运的“道”,它也主宰世界,但其主宰权能有限,似乎只在事业最终结局时,才起类似于命运的作用。
“道”有微弱的人格,有有限的主宰权能,这就在理论思维上,确定了“道”至高无上的地位,没有为“上帝”等神灵创造、主宰、拯救世界留下足够的可解释空间。
《中庸》:“修道之谓教。”现实的人以“道”为信仰,人生就是“修道”的人生,信道与修道统一。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 591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就在忧道、谋道、求道(志于道、担心道之不行、追求道),闻道、明道(认识道、觉悟道),行道(遵循道,实践道),传道、弘道(传播道,弘扬道),不仅让自己人生有道,而且推己及人,仁爱天下,博施济众,让天下有道,总之,人始终、时刻与“道”为一。朱熹将儒家的“道”理解为“天理”。他注解说:“道者,事物当然之理。苟得闻之,则生顺死安,无复遗恨矣。”592将“道”当作自己终身以之的追求目标,将认识、觉悟到的“道”当作自己认识、实践、生产、生活的出发点、准则和理想,当作自己一生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是以“道”为最高信仰的集中表现。
至于修道方法,儒家“四书”之一的《大学》提供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三纲领,是儒家最基本的修道方法。它主张通过内圣(“明明德”)外王(“亲民”,朱熹解释为新民。我以为民,不能理解为民众,而应理解为人,即他人。亲民即新人。明明德是使自己不断明明德而更新,由内而外,明体达用,亲民是帮助他人不断更新而明明德,自外而内,从用到体593),最终达到终极理想的高度(圣人和理想社会)。三纲领具体展开,就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八条目中,修身是关键。内在修养的提高,主要依靠“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其极至便是圣人;内在修养表现在外,推己及人,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极至便是人人均以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
关于儒家的修道方法,如果说《大学》所强调的是内圣与外王、现实与理想的辩证统一,那么,儒家“四书”之一的《中庸》则在天人合一的思路下,从形而上学角度展开了儒家修道方法的全貌。比起《大学》来,《中庸》更加重视内省,更加重视人的内在修养,它将人修养提高的这个问题,分析成为互相不同、但又有内在联系的几个人学问题。《中庸》开宗明义指出: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594
在这里,《中庸》明确地将“天”、“命”、“性”(“天命”之物)、“道”(“率性”之谓)、“教”(“修道”之谓)、“隐微”、“中和”等孔子思想中已经有或逻辑上可能有的几个核心范畴,联系、统一起来谈论,第一次和盘托出了孔子儒家的“一贯”思路,即天人合一(“天命”与人之“率性”、“修道”合一,“诚者”与“诚之者”合一,“诚明”与“明诚”合一)、内外合一(人性、人道与现实人的活动合一)、体用合一(“道”与人合一、“隐微”与“显见”合一、“大本”之中与“达道”之和合一)、主客合一(“天命”之人性与“天地”、“万物”及其运动变化、生生不已、井然有序等合一)的朴素人学辩证法思路。
根据这个思路,孔子提出的关于人的问题,即现实的人通过学习而提高自己的修养,成为真正的、理想的人的问题,获得了明确而清晰的、“一以贯之”的解决。具体说来,“天命”是现实的人之所以必须如此的本体论根据,四个合一则是人事实上可以如此的方法论原则或辩证法根据,从“天”经过人性、修道、教化,达到“中和”境界,则是现实的人成为理想的人,现实的社会成为理想社会的几个必经环节和修养阶段,“中和”则是现实的人修养实现的理想人格的基本特征。而且,人们通过以上的努力,事实上达到的收获,也就是现实的人与自己的真我统一了起来,或者说,现实的人不仅寻找到了自己的真我,而且完全实现了自己的真我。
《中庸》的这一段概括性言论,使孔子人学思想的本体论、方法论、主体论思想都清晰起来,《中庸》由此也成为孔孟儒学形而上学的代表性著作。它提出的许多对立性范畴,如天道与人道、未发与已发、隐微与显见、中与和、诚与明等,都成为后来宋明理学家们反复讨论和发挥的概念。《中庸》第一次将孔孟儒学可能有的本体论提示出来,有力地显示了孔孟儒学理论思维水平可能达到的高度。在形而上学的支持下,儒家修道方法从此就具有了非常明确的根据、出发点、准则、阶段、理想和主体。
关于内在修养提高的方法,孔子提出了“学而时习”、“克己复礼”方法,“学而时习”从认识上解决“格物”、“致知”问题,“克己复礼”则在实践上主要解决“诚意”、“正心”问题。两种方法结合起来,共同推动人的修养的提高和社会的改进。孔子的方法,为后来儒家修道方法提供了大致框架。关于“学而时习”、“克己复礼”,孟子站在个体人成长的立场,将它们统一起来,描述为读其书,知其人的方法,描述为“求其放心”,养浩然之气,尽心知性知天、存心养性事天(正面的方法)和“寡欲”(反面的方法)两个方面;荀子则从社会政治角度,将孔子的方法进一步展开为“虚壹而静”地“诵经”“读礼”方法、在有真正学习心得基础上的循序渐进方法,以及“礼”(社会道德规范)“法”(社会政治制度)的制约。先秦孔、孟、荀三大儒,和《大学》《中庸》一起,将儒家关于现实的人内在修养如何提高的修道方法框架明白揭示出来。后来儒者只能在修道方法的某些具体环节、领域、层次、阶段等方面深化或丰富而已。
在古代儒家学者看来,理性地“志于道”,追求“道”,学习、觉悟“道”,获得、运用“道”,甚至与“道”合一,乃是现实的人成为理想的人的必由之路。在这样的修道方法原则下,宗教性很强的信神灵、信经典等以“信”为主的祈祷、祷告、跪拜等天人联系方式,在中国古代儒家那里只能成为辅助的、次要的方面,在大部分儒家学者眼里甚至可有可无。比如,张载就将“道”理解为“性”与“天”,并明确说:“知性知天,则阴阳、鬼神,皆吾分内尔。”595又说:“舍真际而谈鬼神,妄也。”596张载所说的“真际”,即儒家所谓“道”。经过张载等的讨论,中国古代儒家宗教思想进入一个新阶段:“道”论已经将鬼神观包含在内。不离开“道”谈鬼神,谈“道”即意味着谈了谈鬼神,鬼神观包含在“道”论中,可谓儒家鬼神观的原则。
古代儒家关于修道所达到的理想精神境界,也以理性的现实生活为特征。现实的人具备“道”的信仰以后,其实际的精神状态,恰如张载《西铭》(原名《订顽》)所形象描述的那样:
“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于时保之,子之翼也。乐且不忧,纯乎孝者也。违曰悖德,害仁曰贼。济恶者不才,其践形唯肖者也597。知化则善述其事,穷神则善继其志。不愧屋漏为无忝598,存心养性为匪懈599。恶旨酒,崇伯子之顾养600。育英才,颍封人之赐类601。不弛劳而底豫,舜其功也602。无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603。体其受而归全者,参乎604!勇于从而顺令者,伯奇也605!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存,吾顺事,没,吾宁也。”606
根据张载上述描述,信仰儒家“道”的人,以乾坤为父母,以百姓为同胞、兄弟,以万物为与自己有内在关系者。不要小看自己的身体,它乃是“天地之塞”;不要小看自己的人性,它乃是“天地之帅”。“存心养性”是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富贵乃是支持我“存心养性”的材料,贫贱则是对我“存心养性”的考验,“知化”、“穷神”,乃是我“存心养性”取得成绩的标志,“存吾顺事,没吾宁”,则是我“存心养性”应该具有和将会具有的生活态度。《西铭》正是张载“尽人道则可以事天”607的形象描述。
张载的《西铭》后来受到理学家一致推崇,与它对儒家“天人合一”之“道”信仰的准确生动描述息息相关。二程认为,《西铭》“言极纯无杂,秦、汉以来学者所未到”608,又说:“《订顽》一篇,意极完备,乃仁之体也。学者其体此意,令有诸己,其地位已高。”609朱熹自己承认对《西铭》“信之不疑”,并证明、阐发《西铭》的意思说:
“人之一身,固是父母所生,然父母之所以为父母者,即是乾坤。若以父母而言,则一物各一父母。若以乾坤而言,则万物同一父母矣。万物既同一父母,则吾体之所以为体者,岂非天地之塞,吾性之所以为性者,岂非天地之帅哉?古之君子惟其见得道理真实如此,所以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推其所为,以至于能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而非意之也。”610
“《西铭》之言,指吾体性之所自来,以明父乾母坤之实,极乐天践形、穷神知化之妙,以至于无一行之不慊而没身焉。故伊川先生以为‘充得尽时,便是圣人’。”611
“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本出于儒家经典《礼记》的《礼运》篇,指圣人能够做到这一点,达到这样高的境界。朱熹也用这个说法,表示《西铭》所描述的“天人合一”理想境界。在朱熹看来,这样的理想境界,既根源于“天人合一”的天命流行,也仰赖现实的人对天命流行的“道”的觉悟和实践。“慊”,满足。在“道”的支持下,人“无一行之不慊而没身”,无一事不满足,甚至未留下任何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这样的人生,当然是很美满、幸福的人生。
明代大儒王阳明提出“致良知”命题,将古代儒家心学发展到高峰。他特别发掘了“道”的主体特征,突出了主体在修道以解决信念问题上的地位和作用。王阳明从“良知”角度看《西铭》所述“天人合一”境界,说:
“夫人者,天地之心也。天地万物,本吾一体者也,生民之困苦荼毒,孰非疾痛之切于吾身者乎?不知吾身之疾痛,无是非之心者也。是非之心,不虑而知,不学而能,所谓良知也。良知之在人心,无间于圣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世之君子惟务致其良知,则自能公是非,同好恶,视人犹己,视国犹家,而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求天下无治,不可得矣。古之人所以能见善不啻若己出,见恶不啻若己入,视民之饥溺犹己之饥溺,而一夫不获,若己推而纳诸沟中者,非故为是而以蕲天下之信己也,务致其良知,求自慊而已矣。”612
《西铭》所谓天人合一,万物一体境界,被王阳明看成是“致良知”所达到的理想境界。到这时,人人“公是非,同好恶,视人犹己,视国犹家,而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良知”表现在人际关系上,就是仁爱关怀;表现在国家治理上,就是实行仁政;表现在认识上,就是同情的理解;表现在人格境界上,就是“视人犹己,视国犹家,而以天地万物为一体”。
朱熹用诗句表示人性具有“天人合一”的意境如下:“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昨夜江边春水生,蒙冲巨舰一毛轻。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613“半亩方塘”可谓“人心”的意象,水中“天光云影”可谓“天命之谓性”的意象,“清”为“善”的意象,“源头活水”可谓人“本性”的意象,“春水生”可谓人性自觉的意象,“蒙冲巨舰”可谓各种现实诱惑、私心杂念的意象。儒家理性的人性修养中所蕴涵的天人关系意义,在这首诗中有很生动的表现。
朱熹明确主张“性即理”。这个命题在宗教思想上的意义,用朱熹的话说,就是“性之为德,无所不该,而天之为天,不外是矣”614。天不外于人性,“率性之谓道”,“道”也不外于人性。所以,儒家所看重的理性的人性修养,不仅是理性的追求真理的活动,也是寻找自己人生“安宅”的信仰求证活动,其实就是现实的人成为真正的、理想的人的过程。
于是,从宗教思想角度看,“道”是人们信仰的对象,也特别是人们求证自己信仰必须遵循的辩证法则。朱熹的上述观点,充分体现了古代中国宗教思想以“道”为最高信仰,为人们安身立命之精神家园的特点。


 张茂泽
张茂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