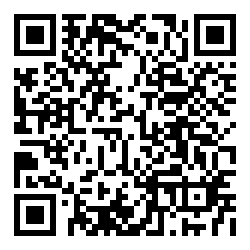张载《西铭》一出,儒学主流即以理一分殊模式诠释其中的一体的仁爱观。只讲“分殊”,“一体”的仁性便沦为“私仁”;只讲“理一”,儒家之一体观就难以与墨子之兼爱、释氏之同体大悲区别开来。故须从“分殊”处“体现”出“理一”,儒学性格由此而得到保证。王阳明从六个面向论说一体之仁,也充分体现了这种“理一分殊”的结构。从存有论上万物为一,一理流行,一气贯通,是为“一”;此为仁之“根”,既曰“根”则必有“端倪”可察(感应之几),必有发生之基础(恻隐之心),必有落实之次第(宗族谱系),必有成长之脉络(政治向度、天人相与),此为“殊”。在亲亲—仁民—爱物,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个殊的脉络里面,充分彰显、体现、实现这个“一”。尽管仔细体味其中的义理,“一体”与“同体”尚有微妙的区别162,但其中的要义却是一个即凸现天地之心、天地生生大德在人身这里得到自觉地体现。人之本心即天地生生之大德的自觉,此为“仁心”。宋明儒以“活”“生”“知觉”来界定此“仁心”,皆是对此生生大德的一种描摹、体认。
然而“天地之心”“生生大德”在人这里的“自觉”“发窍”并不是黑格尔意义上绝对精神意识到它自己,这个“自觉”“发窍”是“镶嵌”在人之“身”之中的。人身即仁身。人身本身就是天地大化流行不已的一个“结晶”,钟五行之灵秀,集天地之精华。故而与天地大化一气贯通、息息相关。
人是天地的“心”,天地则是人之“身”。这里确实涉及天人连续的思维模式,这个天—地—人连续体在生存论上是为而不名的,或者说从未成为显题(thematic)。二程子的话可以引为佐证:“天地安有内外?言天地之外,便是不识天地也。人之在天地,如鱼在水,不知有水,直待出水,方知动不得。”163离开了天地,人身便动不得,便成了尸体。人身活动自如,原来皆是在天地之中方能如此。这样,我们便获得了一个存在链:天地生物之心“发窍”于人心之中,人之心弥漫于人周身之中(“身心一如”),人之身活动于天地万物之中并最终因嵌于天地大身之中而得以活动自如。天人无间断,天—地—人—万物最终亦是身心一如之大生命体。
因此“尽心”必与修身、养身、练身、诚身联系在一起。而每一个“身”都处在天地这个大身子脉络之中的不同的“位置”,这个“位置”都是彼此相贯、相关的“活的单位”,所谓“一体相关”是也。“己身”与“兄弟之身”有同胞之谊,皆从“父母之身”而来,由此上溯,则推至天地之大父母,在天地大父母这里,动植飞潜皆为同胞,皆是自家心头上的“肉”。然而,天何言哉,地何言哉。天地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圣人循天理而欲万物同之”。因此,尽心就是“体”这个“心”,就是要替天地这个大父母为万物操这份心。在人身体力行的过程之中,天地万物遂成了一个“大身体”。
离开“体现”,万物一体就成了一种“臆想”;离开“身—体”(以身体之与体之于身),万物一体就成了一种“光景”。王阳明一体之学是“实学”,其“实”就在于体之于身、验之于心,在亲亲—仁民—爱物这一推己及人的无限过程之中落实、体证一体之仁的“天地生物之心”。


 陈立胜
陈立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