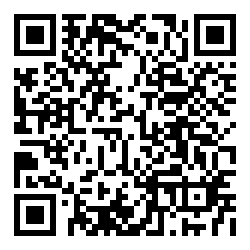马克斯·韦伯是近代社会科学发展史上世界公认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在社会学领域中与卡尔·马克思、埃米尔·迪尔凯姆并驾齐驱。作为一位跨世纪的伟大学者,他在生命的五十多年时间里为后世留下至今尚未全部出版的大量巨著。然而,这位社会学家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在“学术”的思想背后,又有怎样的“生活”背景支撑呢?
与父母终生隔阂的韦伯 韦伯出生在德国的一个有广泛社会和政治联系的家庭。由于其父亲在政界的关系,造就了一种智识性刺激的氛围,对韦伯的成长起了重要作用。父亲老马克斯·韦伯出身西法利亚一个纺织业为主的工商业家族。到小韦伯出生时,父亲已经是一名法官。韦伯的母亲出身于教育世家,关注并研究宗教和社会问题,对下层社会有着深切的同情。老韦伯一直活跃于政界,在政治上倾向于立宪派,由于关心政治,他逐渐成为一个典型的德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两度当选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曾在德意志帝国议院任职,忙碌热衷于当代政治问题,“沉溺于上流社会的美食、自我满足式的自由放任主义”(沃尔夫冈·莫姆森语,转引自迪尔克·克斯勒《马克斯韦伯生平著述及影响》,郭锋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老韦伯虽然是新教徒,但具有享乐主义倾向,同富有宗教责任感和慈善理念的妻子有很大不同。这种精神境界的差异,使得夫妇之间经常发生冲突,家庭失去和睦。母亲在小韦伯心目中的地位重过父亲,所以逐渐对父亲产生抵触情绪。同时,老韦伯对子女的教育方式专制,纯粹用家长制的方式管理孩子,也使小韦伯反感。小韦伯则早熟、孱弱,除了阅读没有别的喜好,在内心深处很难与双亲沟通,“既远离父亲的庸俗,也推开了母亲的敬虔心态”(《韦伯小传》,《马克思韦伯作品集》第1卷第9页)。后来,老韦伯对妻子的独裁专制态度使韦伯忍无可忍,甚至认为母亲的人身安全也受到父亲的威胁。这些最终导致父子之间的关系彻底破裂。
韦伯上大学后,既与父母疏离,又无形中被父母所型塑。在生活中,韦伯下意识地受到父亲现实态度的影响,表现为决斗和酗酒,并由此而挨了母亲的耳光;在学业上,韦伯有意识地接受母亲的宗教信仰熏陶,热衷于神学和哲学的研究,但拒绝对宗教的皈依。前者使他度过青春期走向成人,一扫幼年害羞、腼腆与缺乏安全感的气质;后者使他步入学术殿堂,成为最出色的无神论宗教学家。
少年的家庭生活,拉开了韦伯与父亲的距离;大学的学生生活,又拉开了韦伯与母亲的距离。韦伯在心理上拒斥父亲,却又无形中继承了父亲对现实政治的热情。韦伯在心理上同情母亲,却又拒绝了母亲所期望的虔诚信仰。入伍后的军营生活,使他从内心中产生了对机械式服从命令的厌恶和抗拒,却又改变了自己的习性,并使自己成为一名有统驭能力的军官。了解这些背景,可以恰当解释韦伯一生的诸多矛盾现象。
精神分裂的韦伯 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末章写下了那经久传诵的段落:“没有人知道将来会是谁在这铁笼里生活;没有人知道在这惊人的大发展的终点会不会又有全新的先知出现;没人知道会不会有一个老观念和旧思想的伟大再生;如果不会,那么会不会在某种骤发的妄自尊大情绪掩饰下产生一种机械的麻木僵化呢,也没人知道。因为完全可以,而且是不无道理地,这样来评说这个文化发展的最后阶段:‘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幻想着它自己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等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43页)在后人的分析中,这段话充分显示了一种精神分裂的风格,消沉而痛切,同时又像是睿智而癫狂的预言。
智力往往与焦虑有关。早年时,韦伯曾经患过脑膜炎,这有可能对他产生了无形的生理影响。成长期间与父亲长期的争吵与价值观的冲突,像大山一样压迫着韦伯,让他久久难以释放。1897年其父亲的突然去世,使韦伯失去与父亲和解的机会,让他抱憾并自责终生。而对母亲的敬重却在学业上不按母亲的教诲自行其是,也给他造成内心的隐性歉疚。在父亲去世后不久,韦伯就出现了多种不适症状:疲惫、失眠、内心紧张、自责、间歇性焦虑,有时几乎不能做任何事情。精神上的抑郁与超强度工作、旅游交错进行,加剧了他的身体问题。另外,韦伯的家庭生活屡屡坎坷。起初,韦伯在海德堡大学上学时,喜欢上了姑表妹埃玛·鲍姆加滕,但后来埃玛却患了精神病,不得不中断了这段恋情。但在韦伯与他的姨表妹玛丽安娜订婚后,埃玛却康复了。按照传记作家的记载,韦伯把自己与埃玛的关系及时调整为纯粹的友谊关系,而且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给这位纤弱女孩造成的痛苦。而韦伯与玛丽安娜的恋爱过程一波三折,两人婚后的无性生活,恐怕也给他造成了思想负担。“韦伯与玛丽安娜的结合主要是建立在知识和精神志同道合的基础上的,他们婚后性生活并不成功,韦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才发觉这一点。这是一个极端的婚姻关系,他们婚后一直没有孩子。”(迪尔克·克斯勒《马克斯·韦伯的生平、著述及影响》,郭锋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1页)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韦伯于1897年到1903年之间经历了精神分裂病症的折磨。为病痛纠缠的韦伯只得辞离教授一职,去美国休养兼考察。而这次出行,促成了他的名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诞生。
有句俗语说:所有的天才都是神经病。也许,韦伯这种精神分裂与他对事物的敏感、观察角度的与众不同、分析论证的独辟蹊径都有关系。迪尔克·克斯勒说:“总之,韦伯的病不是那种真正的‘精神病疾病’。复杂的原因和多样的环境因素导致了神经打击的出现。一个自我分析的作品——这部作品现在已不存在——或许会对这些背景原因提供一个有意义的剖析。由于神经症状对韦伯的思考思维有无直接影响无迹可寻,其疾病方面的影响被忽视了。一个事实是,自1889年到1920年(除1901年),韦伯每年都有东西出版。”(同上,第15页)
在音乐中寻找意义的韦伯 韦伯对音乐很感兴趣,常常沉浸在音乐中平息自己的情绪。也许,学者同音乐有某种冥冥之中的联系,爱因斯坦对小提琴的演奏就要比对物理学更着迷。据说,爱因斯坦认为,他的音乐天赋要远远高于研究相对论的天赋。韦伯喜好音乐,但他在音乐上的造诣如何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不过,他从音乐里悟出了更为深刻的道理。他有一篇未完成的大作《音乐的理性基础和社会基础》,这篇文章竟然创立了一个学科——音乐社会学。他的这篇文章不是谈音乐欣赏,而是从理性主义出发,根据文化传承、技术发展、经济状况和社会关系等各种因素来探讨音乐,文章涉及音阶、旋律、律制、乐器、复调、和声、调性等方面的内容。现在的学者一旦谈到音乐社会学,非要把韦伯请出来不可。更有甚者,后来的德国社会学家阿多诺干脆用12卷的巨著来谈音乐,这显然同韦伯的影响有关。在阿多诺笔下,黑格尔之后的资本主义社会就是一个奏鸣曲式的社会。
当我们听取不同的音乐时,韦伯就有可能在耳边提醒我们。例如,中国的二胡琵琶,同西方的提琴黑管之类相比,似乎确实有社会性的差别。而中国的钟磬丝竹之声,则与西方的奏鸣曲交响曲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要真正理解韦伯所说的加尔文教和中国儒教的差别,最好是到维也纳金色大厅听《茉莉花》,再到紫禁城内听贝多芬,感受就会比读书深得多。
(初稿撰写:王艺)


 刘文瑞
刘文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