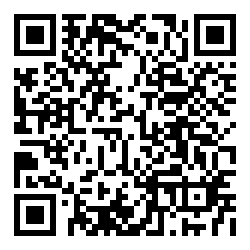从某种意义上说,同为人际关系的协调处理活动,人类的政治活动乃人类的伦理活动的进一步的放大形式。其区别仅在于,如果说后者仅将该协调处理活动局限于我周围的我他领域,那么前者则将该协调处理活动放而大之,推而广之,彰显、泛化到整个社会组织、整个人类社会共同体。这决定了人类伦理学作为人类政治学的“先蕴之原型”,其本质的规定乃为我们洞显出了人类政治学本质的真正隐秘。
因此,正如西方传统的伦理学学说坚持智慧即美德,就其本质而言乃是一种从事实判断导出价值判断的理性主义的学说一样,西方传统的政治学说其本质亦不能置喙这种理性主义之外。这种理性主义的政治学坚持,唯有借助于理性的合乎规律的支配,才能使社会从混乱无序趋于和谐有序,才能使社会从人人的各遂其私、人间的弱肉强食臻至其中一种公我得以申张和维系的社会之正义,其情况恰如在伦理领域唯有借助于理性的自觉,才能使一个人的行为更加合乎人伦之理,才能使人步出自我中心主义的误区而与他人建立起手足之谊的道德伦理关系。
尽管一种系统成熟的政治学说降至近现代才在西方方兴未艾地真正崛起,然而按西方政治学著名学者邓宁、萨拜因的观点,早在古希腊西方哲人就开始了政治学的理论探索的漫漫之旅,并从中天才地揭示出了人类政治生活的一般性的普遍规律。萨拜因称:“我们认为那些希腊人是‘古代的’,只是就我们称呼他们的这个名词所指的意义而言。然而就……在许多方面看来更为正确的观点而言,我们可以准确地称他们是‘现代的’。”88而这种政治学上的“先圣后圣其揆为一”恰恰是通过一种至尊的理性来加以维系的,正是从理性中为我们开出了西方政治学的历久不衰的传统,也正是基于理性才使西方政治学“一以贯之”地把其古代和现代联系在一起。
无疑,正如众所公认的那样,这种古希腊的政治学上的理性主义的致思取向是由柏拉图率先奠定的。在其堪称西方政治学的开山之作《理想国》里,他不仅为我们区分出城邦居民中“爱利者”、“爱胜者”、“爱智者”这三种依次递升的社会阶层,其分别对应于“铜铁”、“白银”、“黄金”这三种品位迥异的人的血统,而且断言“神谕曾经说‘铜铁当道,国破家亡”’,89提出“研究政治艺术的事情天然属于爱智者的哲学家兼政治家”,90从而使理性与政治结为神圣的同盟,遂为西方政治学开出了其唯知主义取向的学术传统。人们看到,待其稍进,这种唯知主义的传统在柏氏弟子亚里士多德的学说里得到了进一步的体现和运用。这种进步除了表现为亚氏将柏氏的沉思性的理论理性改造为操作性的工具理性,并为西方哲学建立了一种不无精密的科学性的逻辑学理论之外,还表现为他以后者为思想工具,对由人这一现实的“政治动物”所构成的城邦政治之成因、秩序、体制、目的、策略等诸多方面予以深入的、实证的分析,遂使一种应用性的、技能性的“政治知识”或“政治科学”得以最终奠定。在亚里士多德的学说里,政治学已不再是柏拉图的“理想国”里所设想的可望而不可企及的极其奢侈的理想之物,而是洗心革面成为一门政治家可操作、可运用掌握的现实的科学。
理性在现实社会的结晶则是法制化。因此,在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中,其“政治学首先是关于政治制度的科学”91,为古希腊先贤毕达戈拉斯、伯里克利等人所率先倡导的法制思想被给予进一步的重申和肯定。在坚持“依从理性,把理性作为行为准则”这一思想的同时,他明确提出“法律恰恰正是免除一切情欲影响的神祇和理智的体现”,“谁都承认法律是最优良的统治者”。92于是,在亚里士多德的学说里,其彻底祛除了尚残存于柏拉图学说中的贤人政治的思想孑遗,而把合理的法制建设视为社会冲突赖以解决、城邦政治赖以成功的真正的秘诀。显而易见,这种用科学的立法来整合社会秩序的思想,不过是其用合理的“形式”而使混沌的“质料”得以构型的哲学思想在社会领域里的体现,是其物理学的理性主义在其政治学上的一种既极具创意又不无酷肖的理论翻版。
就此而言,与其说是理想主义者的柏拉图,不如说是现实主义者的亚里士多德对西方政治学理论传统的影响更为深刻,因为西方政治学众所公认地浸淫于一种所谓的“自由主义”政治传统之中,“自由主义”的原则被其封为圭臬,而这种“自由主义”按曼宁的说法,其首先“相信个人的自由与福祉、社会的正义与安全依赖于所有社会成员的法律关系被清楚地界定”。93然而,就这种以法制为依托的政治理性主义也即政治自由主义来说,亚里士多德所作的工作不过是希声之初启、冰山之一角,该政治理论之真正运会成熟、其思考之真正渐入佳境,则有待于古罗马的自然法理论及其后来的近代社会契约论理论的兴起。
古罗马的自然法理论之所以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不仅在于古罗马人不无忠诚地秉承了古希腊人的理性主义的传统,而且还在于其将该理性极其自觉地运用于广泛的社会政治实践之中,形成了令古希腊人难以望其项背的系统的法典和成熟的法律专业技能。“这样,希腊人的推理天赋,与罗马法学家的专业技术结合在一起,终于发展出一套能为一般人接受的新型法律制度。”94诚如西塞罗所说,这种具有坚实政治实践基础的自然法理论坚持,世界上有两种法律,一种是自然法,一种是人为的成文法,前者为后者之渊源,而后者则以前者为依据,因为后者最终依据于一种与自然适应的最高理性:“事实上有一种真正的法律——即正确的理性——与自然相适应,它适用于所有的人并且是不变而永恒的”,“法就是最高的理性,并且它固植于支配应该做的行为和禁止不应该做的行为的自然之中。当这种最高的理性,在人类的理智中稳固地和充分地发展了的时候,就是法”。95在这里,自然法像自然界中先天自明的数学公理一样,其不依任何人的意志、习俗为转移而为一种合乎理性的先验的法则所规定。而随着法与理的内在勾连、法的合理内核被进一步明确和澄清,滥觞于古希腊政治学说中的法治思想遂宣告在西方文明世界中的正式奠定。自此之后,该法治思想虽然在现实政治中备受人治政治的侵凌,以至于其并未有效阻止罗马帝国君主滥用政府的无上权威,但统治者可以为所欲为之思想却从未在西方政治思想领域里居有一席之位,其故端恰在于由罗马人所确定的自然法的传统之深入人心、其主张之众望所归。
然而,在漫长的西方中世纪,由于教会的长期统治及影响,这种自然法理论一直是与基督教学说联姻在一起的,而其所坚持自然的理性乃是一种考文所谓的“上帝赐予的理性”而具有突出的神启性质。这决定了随着西方近代神界向俗界转移这一俗世化运动的兴起,自然法亦应相应地转换和更新其哲学理论基础。而近代社会契约论的迅速崛起恰恰满足了这一时代所需,它对传统的自然法理论给予了一种人文主义的还原,以人性而非神祇重新论证了其理论的正当性。但这种理论的转换并非从根本上改变传统自然法的理性主义性质,而是把契约论看作是自然法的一般原理之具体实现方式,在近代俗世化运动这一新的历史条件下对该性质给予一种更为深入,也更为贴近现实的学理上的说明。
考之西方近代社会契约论的历史,就不能不远溯到晚期希腊的伊壁鸠鲁的理论。而伊壁鸠鲁之所以被包括马克思在内的众多思想家册封为社会契约论的真正鼻祖,首先在于其“原子偏斜运动理论”的提出使他不仅在西方哲学史上第一次肯定了宇宙的偶然性,而且正如卢克莱修所断言的那样,他打破了“命运的束缚”而为现实中的个人活动的自主性张目,提出无自由便无责任而恢复社会中每一个人所应负起责任的自由,从而为一种坚持自由和民主的社会政治观提供了哲学基础。同时,在其学说里,这种对必然命运的积极反抗又不意味着断然拒绝社会政治上的理性主义,而毋宁说从总体的独断的理性主义走向个体的反思的理性主义,把社会政治理性视为基于互利的思考个体自主、自觉缔约的结果,而“公正”的国家和法正是这一社会契约活动的具体产物。这样,经由伊壁鸠鲁的理论努力,西方政治学一方面恢复了政治上的个人自由的无上尊严,另一方面又为政治上的社会法制的发展开拓出巨大空间,作为西方近现代自由主义政治的拱顶石的自由和法制这一双子星座早在希腊人的视野中就已赫然显现。
因此,包括为格劳秀斯、霍布斯、斯宾诺莎、洛克、卢梭在内的众多西方近代思想家所提出的所有的社会契约论理论实际上都不出伊壁鸠鲁学说之左右。无论这些契约论学说其表述方式多么林林总总,其理论之基础、重心、结论如何各自不同,其中有公利主义的契约论或公意主义的契约论、积极的契约论或消极的契约论、集权的契约论或分权的契约论、绝对政府的契约论或有限政府的契约论等等,但它们都坚持国家乃为由每一个人参股的“股份有限公司”,即主张以“自然状态”的个人为社会契约的起点,以反思的、自觉的理性为使个人整合为公我的社会手段,它们都借近代启蒙主义之助,把国家、政府和法律之公正看作是普遍的、合理的宇宙真理在人类社会中的体现。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都不失为一种亚当·斯密式的“看不见的手”的理论。但其区别于中世纪的自然法的政治理论的是,如果说在后者之中这只“看不见的手”是由冥冥之中的上帝暗中操纵的话,那么对于前者来说,在启蒙之光的照耀下,它已彻底处于无蔽之中,它已不复有任何神秘的特性,以至于最终完全由人类这一历史的新主人对之亲手掌控。
这样,殆至西方近代,西方的政治学的理性主义理论传统经由古代的宇宙论的理性主义、中世纪神学的理性主义以及近代的人本的、反思的理性主义已羽翼丰满,而包括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在内的众多现代西方新政治学理论实际上都不过是这一传统的后续性的拓展。与此相对应的是,在现实生活中以自由、民主、法制为旗号的自由主义的宪政亦日益成熟,遂使人类完全、彻底地告别了漫长的专制王权的黑暗蒙昧统治。然而,物极必反,这种政治理性主义的不断发展最终又不能自已地导致了其一种“辩证的反转”。而这种辩证的反转,按哈贝马斯的说法,即“证明的形式条件自身就获得了合法化力量,理性协议本身的程序和假设前提变成了原则”96这一人类政治生活异化的产生。换言之,理性本身乃为人自身服务的工具性手段,然而随着这一手段日益强大,其也日益反客为主地将人自身玩弄于其股掌之中。在西方现代政治生活中,这种“启蒙的辩证法”在导致作为社会生活的德性目的渐趋蔽而不明、渐趋退居和龟缩于私人化的宗教生活领域的同时,还导致了亨廷顿所谓的“权威的合理化”、霍克海默所谓的“社会的操纵意识”、狄尔泰所谓的“政治机械主义”在西方社会的节节胜利,主张每一个人可以自决的西方传统的政治自由主义遂让位于服从理性独白原则的一元独断的社会技术性统治,让位于一种阿伦特所说的“无人统治”,或一种托克维尔所说的“软性的独裁”或“多数人的暴政”。而现代德国所出现的法西斯主义的国家社会主义这一新极权主义即其最具极端的形式。这一切表明,西方政治理性主义的发展虽使人类社会告别了蒙昧、野蛮的“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但“不可抗拒的进步过程就是不可抗拒的退化过程”(霍克海默语),与此同时又将人类社会重新置于一种更加不可理喻、更为非人化的“利维坦”这一政治巨兽的新的威胁之中。


 张再林
张再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