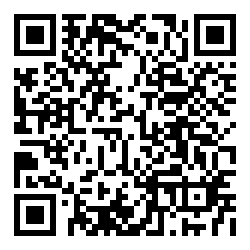在康德的著作中,「通常的人类知性」一词往往与「通常的人类理性」(gemeine Menschenvernunft)、「健全的人类理性」(gesunde Menschenvernunft)、「健全的人类知性」(gesunder Menschenverstand)互换其词。它们均相当于英文中的common sense 一词,而可追朔到当时以莱德(Thomas Reid, 1710-1796)、欧斯瓦尔德(James Oswald, 1703-1793)、比提(James Beattie, 1735-1803)、史蒂瓦尔特(Dugald Stewart, 1753- 1828)等人为代表的苏格兰「常识哲学」(common sense philosophy)。在康德的知识论系统中,「理性」与「知性」分属不同的层面,各有其功能,但在目前的脉络中,「理性」与「知性」二词却可以互换。
康德所谓「通常的人类知性」是指一般人未经哲学反思──或者说,「百姓日用而不知」──的认知或意识。他在1783年出版的《一切能够作为学问而出现的未来形上学之序论》一书(以下简称「序论」)之末章对这个概念提出了如下的说明:
1) 〔……〕健全的知性是什么呢?它就是通常的知性(就它正确地下判断而言)。而通常的知性是什么呢?它是认知与具体地运用规则的能力,而有别于思辨的知性──它是抽象地认知规则的能力。故通常的知性几乎无法了解 「一切发生之事系藉由其原因而被决定」这项规则,而且决无法如此普遍地理解它。因此,他要求一个来自经验的例证,而且当它听说:这无非意谓「每当它见到一片窗户玻璃被打破或是一件家用器具消失时,它所想到的东西」之际,它就理解这项原理,而且也承认它。因此,除非通常的知性能见到其规则(尽管这些规则实际上是它先天地所具有的)在经验中得到证实,否则它没有其它的运用;是故,先天地且无待于经验地理解这些规则,是思辨的知性之事,而且完全在通常的知性底视野之外。但是形上学确实仅与后一种知识有关;而且诉诸那个在此完全无所判断的证人──除非我们身陷困境,而且在我们的思辨中得不到建议与协助,否则我们一定会鄙视他──,的确是健全的知性之一项恶兆。472
康德在此将「通常的知性」(健全的知性)对比于「思辨的知性」。由康德的说明可知:他所谓「通常的知性」是一种局限于经验之中的认知能力。这种能力只能把握具体的经验,而无法理解形上学的原理(如因果律);而我们要理解形上学的原理,就得靠「思辨的知性」。
在《序论》的〈前言〉中,康德直接提到莱德、欧斯瓦尔德、比提等人,并且对他们提出如下的批评:
2) 〔……〕他们发明一种全无理解而刚愎自用的省事办法,即诉诸通常的人类知性。事实上,拥有一种正直的(或者像人们近来所称的,纯朴的)人类知性乃是一项伟大的天赋。但是我们要证明这种天赋,必须藉由行动(Taten),藉由深思熟虑且合乎理性的思想和言论,而非在我们无法提出任何明智的理由为自己辩解时,将这种天赋当作一种神谕而诉诸它。在理解和学问都无能为力之际,然后(而不在这以前)才诉诸通常的人类知性,这是近代的精巧发明之一。由于这项发明,最无聊的空言之辈得以自信地与最深刻的才智之士分庭抗礼,并且与他相持下去。但只要尚有一丝理解残存,我们一定会避免利用这个应急之方。严格说来,诉诸通常的人类知性无异于诉诸群众底判断──这是一种喝采,哲学家为之脸红,但是耍小聪明而大受欢迎的人却为之扬扬得意而刚愎自用。可是我应当想到:休谟也能像比提一样,要求于一种健全的知性,此外还能要求于比提一定没有的东西,即是一种批判的理性──这种理性节制通常的知性,使它不会擅自进行思辨,或者在仅论及思辨的情况下不会想有所决定,因为它无法为它的原理提出辩解;只有这样,它才不失为一种健全的知性。凿子和槌子极适于用来处理一块木料,但是对于铜雕,我们就得使用蚀刻针。故健全的知性和思辨的知性一样,两者皆有用,但各以其道。当问题涉及直接应用于经验中的判断时,前者有用;但是当我们应当一般性地、纯由概念去下判断时,譬如在形上学中,后者有用。在形上学中,自命为健全的(但往往作为反义语)知性完全无法下任何判断。473
这段引文与上一段引文的意涵大体相同,但是康德在这段引文中进一步强调「思辨的知性」之功能,即是:它可以节制思辨的知性,使之不会僭越其权限,而在经验的领域之外进行思辨。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分析西方传统自然神学中的「上帝」概念。他指出:传统的自然神学将「上帝」界定为一个「最实在的存有者」(ens realissimum)之理念(Idee),这是一个「先验的理想」(transzendentales Ideal)474。我们的理性必然要求这个理念,因为它是一切概念决定(Begriffs- bestimmung)之形式条件。但是这个理念并无法提供任何知识内容,也无法成为知识的对象。然而,传统的自然神学却将这个理念先是「实在化」,继而「实体化」,最后「人格化」,由此产生一种「先验的幻相」475。「思辨的知性」可以防范这种幻相,故又可称为「批判的知性」。
最后,康德在《序论》的结尾针对「通常的人类知性」作了以下的总结:
3) 〔……〕在作为纯粹理性底一门思辨学问的形上学之中,我们决无法诉诸通常的人类知性;但如果我们被迫离开形上学,而且放弃一切纯粹思辨知识(它始终必须是一种知识),因而也放弃形上学本身及其教益(在某些事务上),并且唯有一种理性的信仰被认为对我们而言是可能的,也足以满足我们的需求(或许甚至比知识本身更有益),则我们或许可以这么做。因为这样一来,事情底态势便完全改观了。形上学必须是学问,不仅就整体而言,也就其所有部分而言;否则它什么都不是。因为就它为纯粹理性之思辨而言,除了在普遍的洞识之中,它无处立足。但是在形上学之外,或然性与健全的人类之性或许有其有利的与合法的运用,但却是按照完全独特的原理──这些原理底重要性总是系乎对于实践事物的关系。476
康德在这段引文中所提到之「理性的信仰」(vernünftiger Glaube)一词即相当于他在1786年发表的〈何谓「在思考中定向」?〉(“Was heißt: Sich im Denken orientieren?”,以下简称「定向」)一文中所提到之「理性底信仰」(Vernunft- glaube)。这篇论文旨在探讨上帝存在之可能论证。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分别批判西方传统神学所提出的三种上帝论证(存有论论证、宇宙论论证、目的论论证),并且归结说:这些上帝论证都是建立在先验的幻相之上。总而言之,单凭思辨理性,我们既无法肯定、亦无法否定上帝之存在。依康德之见,人类的知识仅局限于可能经验的对象;或者如康德自己所说,「对于事物底知识,范畴除了应用于经验对象之外,并无其它的运用。」477因此,如果理性要思考超经验的对象(如上帝之存在),就无法根据知识的客观根据(即范畴),而只能根据一项主观原则去下判断。这项主观原则即是一种对理性底需求的感受。
在理性之理论性运用与实践性运用当中,「理性底需求」均有其功能。在其理论性运用中,「理性底需求」主要是为了在知识的客观原则不足的情况下「确认」(fürwahrhalten)上帝的存在。在这个脉络中,「上帝」的概念属于一种主观的形式条件,藉以使我们的知识在一切可能经验的界限内尽可能地达到完整性与系统上的统一性。这种条件康德称为「理念」,而上帝的理念则特别称为「理想」。在〈定向〉中,康德将「上帝」概念之形成过程描述如下:当我们为了达成知识之系统性统一而必须使用一个概念(如「上帝」概念),而这个概念在直观中又无任何与之相符合的对象时,我们唯一能做的便是:先根据「一切判断之最高原理」(即矛盾律)来检查这个概念,确定它不包含矛盾;其次,将这个超越经验的对象与经验对象之关系置于范畴之下,以便至少以适合于理性之经验运用的方式来思考这个超感性之物。然而,单是藉由「上帝」的概念,我们对于上帝的存在及其与宇宙(可能经验的所有对象之总合)间的实际联系依然无所知。至此,我们可以说:「上帝」的概念在概念上是可能的。在这个脉络中,由于「理性底需求」之介入,「上帝」的概念不仅在概念上是可能的,而且在理论上也是必要的478。康德将这种需求称为「纯粹的理性假设」(reine Vernunfthypothese)479。
然而,「理性假设」仅是有条件地必然的,这就是说,唯有当我们想要说明宇宙中的秩序与合目的性时,我们才必须预设上帝的存在。反之,在其实践性运用中,「理性底需求」却是无条件地必然的,这就是说,「我们之所以不得不预设上帝底存在,不仅是由于我们想要判断,而是由于我们必须判断」480。更确切地说,「上帝」概念之无条件的必然性在于我们促进「最高善」――亦即道德与幸福之成比例的结合――的义务,如康德在〈定向〉中所言:
4) 因为理性之纯粹实践的运用在于道德法则之规定。但是道德法则均导向在世界上可能的最高善(就它单凭自由而有可能性来说)底理念,亦即道德(Sittlichkeit);从另一方面,它们也导向不仅关乎人类自由、而是也关乎自然之物,亦即最大的幸福(就它依道德底比例而被分配来说)。如今理性需要假定这样一种有依待的最高善,而且为此之故,假定一个最高的智性体(Intelligenz),作为无依待的最高善――并非为了由此推衍出道德法则之约束性威望或是遵从道德法则的动机(因为如果它们的动因不是单从本身确然无疑的道德法则被推衍出来的话,它们就不会具有任何道德价值),而仅是为了赋予最高善底理念以客观实在性,也就是说,防止最高善连同全部道德仅被视为一个纯然的理想(如果某个东西底理念不可分离地伴随道德,而这个东西却不存在的话)。481
这段文字虽然简略,但其意涵却很清楚。后来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的〈纯粹实践理性底辩证论〉中有更详细的说明,我们可以将其论证重述如下:我们的实践理性必然要求「最高善」,即德行与幸福之一致,这是一项道德法则。但是在现实世界中,有德者未必有福,而道德法则又不可能是虚假的;这便使我们不得不「设定」(postulieren)灵魂在来世的继续存在,俾使德行与幸福有可能在来世达成一致。而为了要保证德行与幸福之一致,我们又必须「设定」一个最高的智性体之存在。这个最高的智性体一方面必须具备足够的智慧,能根据人类行为背后的存心来判定其道德性,另一方面必须具备足够的能力,能按照人的德行来分配他所应享有的幸福。换言之,惟有全知全能的上帝才足以保证福德之一致。这便是康德对上帝存在的「道德论证」。
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将这种藉由「道德论证」而「设定」的上帝存在,连同意志之自由与灵魂之不灭,称为「纯粹实践理性之设准(Postulate)」。在〈定向〉中,康德则将这种「上帝」概念称为「理性底信仰」,以对比于「理性底洞识」(Vernunfteinsicht)与「理性底灵感」(Vernunfteingebung)482。所谓「理性底洞识」涉及康德在〈定向〉一文中对门德尔颂(Moses Mendelssohn, 1729- 1786)所提出的批评。在该文的开头康德便提到:门德尔颂在《黎明,亦名论上帝存在之演讲录》(Morgenstunden oder Vorlesungen über das Daseyn Gottes, 1785)及《致雷辛底友人》(An die Freunde Lessings, 1786)中明白地信从「在理性底思辨运用中藉由某种引导工具来定向的必要性之格律」,而门德尔颂有时称这种引导工具为「共感」(Gemeinsinn),有时称之为「健全的理性」(gesunde Vernunft),有时又称之为「纯朴的人类知性」(schlichter Menschenverstand)483。康德一方面虽然承认门德尔颂的贡献在于坚持「仅在理性中寻求一项判断底可容许性之最后试金石」484,但另一方面又惋惜门德尔颂不了解他自己所诉求的引导工具「并非知识,而是理性之被感受的需求」485。如果联系到康德对苏格兰「常识哲学」的批评,我们可以从康德的立场说:门德尔颂之错误在于欠缺「批判的理性」之节制,因而将理性之主观原则(理性底信仰)误认为客观原则(理性底洞识)。在这个脉络中,我们才会理解康德在引文(3)中所言:「在形上学之外,或然性与健全的人类之性或许有其有利的与合法的运用,但却是按照完全独特的原理──这些原理底重要性总是系乎对于实践事物的关系。」换言之,在思辨哲学中不足为据之「通常的人类知性」在实践哲学中却大有发挥的余地。


 杨儒宾
杨儒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