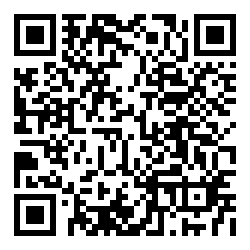假如一个人可以独自生存,那他是不需要指称的,他直接用手做事就行了。指称发生于人际之间,发生于交往活动中。用“手指”“指谓”某个东西,是要让别人注意它,乃至让大家共同关注,一起“盯住它”或“抓住它”。当事人的指称活动是能够为相关主体直观并意识到的,即使开始未必理解它所指称的含义,也能够通过当事人一连串的身体动作、表情和声音而领会其意图,给予回应。随着人们的某种举动与一定对象之间的关系的重复发生,包括对这种举动的模仿和学习,这种举动的功能性意义也就获得了公认,获得了某种普遍性、公共性。所以,手指的指称活动不止是能指与所指、虚与实的统一,还是包含个体性与公共性等多重属性的文化符号活动。
人是社会生物。这一命题表达的内容是极其丰富的,并且永远是开放的、无止境的。人的社会性即使有高等动物“合群性”的生物学根源,其社会性也更多地属于人们在后天的共同生活和交往活动中获得的规定性,一种经由各种联系、作用、制约和相互规定,而形成的超出人与生俱来的生物性的社群性和人格特征,体现在人的显性的肢体动作、面部表情、穿戴打扮,和隐性的心理与意识这两个方面。人们的共同生活,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都离不开生产的分工合作,离不开男女之间的结合以及家庭成员的相互依赖、互助合作,也离不开人们以各种方式展开的交往活动。这种共同的生活和交往活动,在推动人们的生理需要发展为包括“欲望”“希望”在内的社会性需要的同时,也推动着人的自然情感向着“爱”、“信任”和“友谊”的提升,以及“利他”和“公平”的道德意识的萌生;被他人和群体关心和承认的需要,促成了人的荣誉感、尊严感甚至虚荣心的产生;群体内部的相互作用、竞争和与其它群体争夺利益的需要,则激发出人们争强好胜、出人头地的意识,乃至英雄意识和权势意识等等。由此,人们从趋利避害、趋乐避苦、恋生畏死的“第一天性”中生发、转换出“第二天性”,不仅有了复杂的心理活动、意识活动,还学会了以肢体、表情来“表现”、“表演”,证明自己的存在和才能,人的生活的样式和意义由此变得丰富,但同时也产生了动物的生存所不曾具有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如虚伪、作假)。如同人的灵活的手和手指,能够做不同的事情,也能够表达相反的意思:或获取或放弃,或接受或摆脱、或招呼或拒绝、或赞许或指责、或示好或示威等等,人们的心理、意识也会由于愿望的实现或落空、情感的顺畅或不遂、意志的贯彻或受挫、行动的成功或失败,而生发出相反的“意向”:快乐或痛苦、欣悦或愤怒、羡慕或嫉妒、敬仰或鄙视、感恩或怨恨、满足或遗憾、得意或懊悔、骄傲或谦卑等等。一般而言,人与人的关系既有竞争又须合作,所以,人的身体的符号活动也不可能只是表达单方面、单向度的意义。
但是,人毕竟直接生活在各种共同体中,共同生活所要求的首先是他们彼此的合作而不是竞争,即使竞争,也要以是否有利于合作、是否“合乎情理”作为其准绳和限度。一方面,共同体成员之间的相互依赖、信任、理解、协助和彼此默契,决定了共同体的整合或整体化程度,另一方面,共同体的整合或整体性又反转来要求并促使其成员之间的合作,包括行为的协调。所以,在共同体中,每个人既自己规定、塑造自己,又相互规定和塑造;即使他们个人的身体活动是他“个人”自主地作出的举动,这一举动也不止体现他个人的生命意志,还要体现与他共同生活的其它人的生命意志,以及他们在共同生活中所形成的集体意识或“集体无意识”,包括基本的生命信念、思维方式、生活态度等等。米德指出:“某人作为人存在,因为他属于一个共同体,因为他接受该共同体的规定并使之成为他自己的行动。他用它的语言作为媒介藉此获得他的人格,然后通过扮演所有其它人所具有的不同角色这一过程,逐渐取得该共同体成员的态度。在某种意义上,这便是一个人人格的结构性。各个体对某些共同的反应,当个体影响其它人的时候,那些共同的反应便在他身上唤醒,就此而言,他唤起了他的自我。”“当然,我们并非只是人有我有:每一个自我都不同于其它任何一个自我;但为了使我们能成为一个共同体的成员,必须有一种共同的结构性,……在我们自己的自我与他人的自我之间不可能划出严格的界限,只有当他人的自我存在并进入我们的经验时,我们自己的自我才能存在并进入我们的经验。个体只有在与他的社会群体的其它成员的关系中才拥有一个自我;他的自我的结构性表现或反映了他所属的社会群体的一般行为型式,正如其它属于这一社会群体的每一个体自我的结构性一样。”677具有相对性、反身性和“互文性”这一共同结构的自我,使得共同体中的每一成员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表征这个共同体,即都可以视为这个共同体的符号。这样,人们在社会活动中形成的各种动作,言谈举止、表情声音,就不再是纯然生物性的活动、本能的表现,而成为具有指称、象征意义的社会性“行为”,此即身体的符号活动,也是文化活动。凭借这种活动,人们越来越自觉地展开竞争与合作,产生出相应的交往规则和行为规范,形成一定的社会生活秩序;这些规则、规范和社会秩序又反转来成为对每个人发挥教化和规范作用的风俗习惯、文化环境。——可见,人的社会文化性存在和生活是随着身体的符号活动而建构起来的;身体符号既在特定的“语境”即人们的交往关系中产生,又是这一关系得以形成和发展变化的极其重要的能动的要素。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人的身体符号只是表现共同体或族群的“共性”,表征生存于其中的社会“整体”?而无关人的个性和差异?上面的论述似乎给人这样的印象,但其实并非如此。如果那样的话,任何物种的个体都是这一物种天然的“符号”,符号也不复是人为的东西,不具有人文化成的文化意义,更谈不上创新和发展了。
其实,人们的社会性不仅意味着他们的相互依赖、共同生存,还意味着包含差异、个性的互动和互补。由于先天和后天条件的差异,个人努力和取向的不同,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是绝对的,每个人的身体状况和心理意识都有其特殊性,其感觉和意识、生命和生活更不能相互替代;由生产分工和社会分化所决定的人们的角色、身份、责任和义务也是不同的,而这又会导致或强化他们不同的性格和思想意识的差异。人们共同的生活和社会交往不可能使他们之间的差异消失于无形,相反会造成更多的、更细密的差异和区别。只不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竞争就有合作、有分化就要整合,因而,与差异性相伴随的,也必定有统一的行为方式(如传统社会中繁复的礼节)甚至某种平均化的发生。如果说,在传统共同体特别是家庭内部,高度的利益一致性所形成的“我们”的认同意识和平等意识,自觉不自觉地限制着他们的社会分化,借用黑格尔的话说,家庭是一个直接的伦理实体,在其中个体与整体难以分开,其伦理的身份差异仿佛是自然赋予、与生俱来的,不具有选择性和自为的价值,所以个人的身体活动所体现的只能是共同体的整体性,那么,在人们借助商品经济走出传统共同体的现代社会,“我们”分化为一个个的“我”,成为众多具有独立意识和意志自由的个人,这些个人一方面以契约的形式联系起来,另一方面又通过货币、权力和话语等媒介实现着彼此之间的交往互动,这样,人们的身体符号活动就不止是民族或族群的表征,而同时还会体现出自己的个性和创意。世上没有长相完全一样的人,也没有完全一样的身体活动。身体符号不同于文字符号,就在于它的“亲身性”、“具相性”,它不仅依托于个人的生理方面并表现出属于个人的特点,其身体的动作和表情的直接性,还会将一种感情的因素、交往的意识注入人们对它的理解和反应之中,有助于形成社会生活的规则和风俗习惯。
米德为了论证自我的社会性,突出自我与身体的区分,他说,身体可能以智能性很强的方式活动,而无需一个包含在经验中的自我。自我以自身为对象,这个特征把它与其它对象和身体区别开来。身体的各部分完全不同于自我。我们可以失去身体的某些部分而不会严重侵害自我678。“自我”固然是能够将人的一切身体活动给予统治摄的心理意识现象,因而它不同于具有明显的生理实体性的身体,但意识与人的身体的区分只能是相对的,将这一区分绝对化,人的身体就与单纯的生物的肉体无异,自我意识也成了非生命的虚幻想象,这就重袭了柏拉图的“灵肉”二元论。米德认为,自我的“自私的一面”与“无私的一面”应该用自我的“内容”与自我的“结构”分别来说明,自我的内容是个体的,因而是自私的或自私的根源,自我的结构是社会的,因而是无私的或无私的基础679。这当然有一定道理,但正如他将“身体”与“自我”对立起来,他把自我的“内容”与“结构”、“个体”与“社会”也完全对立起来了!这却属于极端之论,也把问题简单化了。我们既可以说人的肉体“联系着一切的恶德”,也可以说它是人类的慈悲、仁爱之源。所谓“同情”之心、“不忍”之心,既源于生命的天性和直觉,又是针对人的肉体遭受的痛苦而言的。中国大哲老子说:“何谓贵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人所遭遇的祸患首先是身体的祸患,所以,防患就要防身、贵身。老子接着说:“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以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680身体是人的一切目的性活动的起点,也是一切目的性活动的终点;基于“以身观身”的逻辑,才能“以家观家”、“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反之亦然。这就是身体符号给人们的重要启示。所以,我们既以“身体性”(或“亲身性”)又以“公共性”来表示人的符号活动的性质。这里的身体性或亲身性不外于公共性,公共性不是抽象的普遍性或同一性,而是包含个体身体差异及特殊性在内的人们身体符号的相通性、兼容性,它最大限度地包容了每个人的个性与自由。俱乐部就是这种公共性最好的寓所和体现。或许我们还可以通过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性”来理解符号源于人的身体活动的公共性。


 杨儒宾
杨儒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