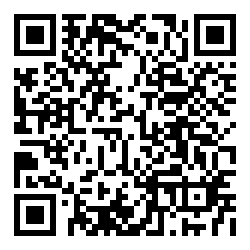——兼及中国哲学的创造性转化议题
张兵
(陕西师范大学 政治经济学院,陕西 西安 710032)
摘 要:立足于中国古代身体观,“体知”所涵括的“身体能够知道”的义项与西方认知理论中“具身化认知”的新进展相一致,但不同于西方认知科学中向经验的彻底回归以及仅仅将身体看作认知的基础,“体知”也是在高层次上对事物复杂性的研究。更为重要的是,“体知”之“知”在于“身体自然知-‘道’”,则“体知”不是一个纯粹认识论的范畴,“体知”之“体”的动、名词区分,显示了作为隐暗维度的“气”,这一“存有的连续”的一体之本然是“‘体知’何以可能”的本体论基础,同时,在此框架下,“身体自然知-‘道’”也体现出修身哲学中“不待修饰把捉”这一实践工夫的独特的理论内涵。因此,作为一个“新”词,“体知”能自然地相承于古代话语,又顺畅地契入于当代生活,可视之为中国哲学创造性转化的一个典范。
关键词:体知;知;体;修身
由杜维明先生提出并极力提倡的“体知”观念,已经受到更多人的关注,并在学术讨论上有着积极的反应337,乃至有人已将其作为一个哲学研究中的基本概念去诠释一些实践领域中的问题。然而,作为一个“新”词,“体知”的关键问题,诚如杜先生自陈,“是一定要在理论构建上有突破,而不仅仅是一个实践层面上的问题”。338在“体知”的理论建构上,首先需要廓清的是“‘体知’何以可能”的问题,指向的是作为其隐暗维度的本体论基础。与此发问相应,此“何以可能”亦关涉到以“体知”所标示的中国传统哲学创造性转化的效度,即其作为一套现代话语系统,能自然地相承于古代话语,又能顺畅地契入于全球化背景下的当代生活,同时,这一与当代生活的契接无碍,必要在实践工夫上显示出其独特的理论内涵,即作为“体知”的“修身”实乃“身体自然知—‘道’”这一为己之道。
一、“体知”语辨
以系谱学的方法对“体知”进行历史的考索,对于“体知”之源的探察,虽非最究底之处,却也不是可有可无。据相关考证,“体知”一词最早出现于《后汉书·志第一·律历上·律准》:“音不可以书以晓人,知之者欲教而无从,心达者体知而无师,故史官能辨清浊者遂绝。”339然亦仅几处可见,故可谓在古代文本中,“体知”系不彰之词。与“体知”意相关而常见者,有二程对“天理二字”的自家“体贴”,延平教朱熹对“喜怒哀乐未发时作何气象”的“体验”,等等。语相似者亦可观朱熹关于横渠“体”字义析:
问:“‘物有未体,则心为有外’,此‘体’字是体察之‘体’否?”曰:“须认得如何唤作体察。今官司文书行移,所谓体量、体究是这样‘体’字。”或曰:“是将自家这身入那事物里面去体认否?”曰:“然。犹云‘体群臣’也。伊川曰‘‘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是这样‘体’字。”(《朱子语类》卷九十八沈僩录)
在宋明儒学中,察、味、认、体、会、证、验等词与“体”的搭配使用更为常见,其中“体验”尤为杜先生所重,乃至其屡称中国古代哲学为“体验之学”340。因此,当杜先生于1984年首揭“体知”之义,有学者戏谑称其为“杜维明所撰”,在“体知”义解上亦可说得通,及称“它(体知)能为我们生活里所熟悉的经验模式提示一个新层面的认识”341,给人耳目一新之感,此“新”则需有辨。
与此辨相关者,还有关于杜先生最早提出“体知”一词的时间考证,以往多集中于杜先生本人写作的中文文献,考虑到杜先生双语写作342,且英文文献又占较重比例这一实情,这一考证是不够周全的。中文文献中,最早阐述“体知”是在1984年,针对王弼“‘圣人体无‘何以可能’”这个难题,作者做了一个认知方式上的区分:“英国哲学家赖尔(G·Ryle)在其《心的概念》(The Concept of Mind)一书中指出‘认知’(to know that)和‘体知’(to know how)的分别。”343这一分别,在1981年的英文文献中已经提到,且用来分析“自我认识”(self-knowledge),344而“自知”、“知人”是杜先生在阐述“体知”内涵时经常举的例子。事实上,更早的英文文献出现在1976年,在探究宋明“身心之学”的体验特色时,作者区分了“如何”(how)和“什么”(what)的问题,进而指出宋明儒学强调的是体验性的理解而非纯认知性论证的技巧。345也是在这篇文章中,杜先生首次将“体”看作探讨宋明儒学的关键性概念,并逐一详解了“体察”、“体味”、“体认”、“体会”、“体证”、“体验”这些以“体”字开头的复合词的含义。
虽然“体知”的提出源自赖尔对知的两个区分,但相对于波兰尼(Michael Polanyi)的personal knowledge(亲知)和the tacit dimension(默会的维度)而言,赖尔的“knowing how对于捕捉‘体知’的韵味还是显得太浮泛、太笼统了”。346因此杜先生后来常用personal knowledge来解释“体知”。一个值得一提的细节是,中文版《杜维明文集》(收录了杜先生英文的中文译本)中,“体知”一词出现的文章,按发表时间计,最早的乃是1975年刊于美国《人文》杂志的The Value of the Human in Classical Confucian Thought(《先秦儒家思想中的人的价值》),其中译者将原文的a personal knowledge of the good译为“一种对善的个我体知”。347此外还可举出一个例子,后来被杜先生亦拿来指示“体知”的传统术语“明明德”之“明德”,杜先生用英文将“明明德”解释为to cultivate our personal knowledge。348personal knowledge在杜先生的访谈中间或名之为“亲知”、“真知”、“个人之知”;他曾引用伊川“虎伤人”的话头来说明观念与亲身经历之间的关联性349,此语亦常被究“体知”者引用,原文如次:
真知与常知异。常见一田夫,曾被虎伤,有人说虎伤人,众莫不惊,独田夫色动异于众。若虎能伤人,虽三尺童子莫不知之,然未尝真知。真知须如田夫乃是。故人知不善而犹为不善,是亦未尝真知。若真知,决不为矣。(《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第二上》)
但“亲知”虽突出了“知”的“亲身体验”或“设身处地着想”的意思,但仍然“未能申明修身哲学的精微之处”350,相较而言,embody是一个更恰当的词,“体知”也就对译为embodied knowing或embodied knowledge。351同样,embody一词在杜先生的英文文献中亦很早出现,“embody” the way即中文的“体道”352,“体”的直接意思是“体现”(to embody)353(此两处所引之文作于1976年)。作于1970年的The Unity of Knowing and Acting: From a Neo-Confucian Perspective(《从宋明儒学的观点看“知行合一”》)一文,更强调了embody一词所具体的“知”之非纯知的特征,其中一句释《孟子·尽心上》“尽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则知天矣”语中的“知”,此处有必要将原文列出:
The word chih(“know”) in the present context connotes not only cognitive knowing but also affective identifying or experiential “embodying”.354
今将其译为:
此处,“知”这个词不仅仅指认识上的知,同时也意味着情感上的认同或经验上的“体现”。
因此,以embodied knowing表达的“体知”包含了递近的三层意思:(1)体验也是一种知,“知”在这里表达的是体验的普遍性及其可被知的公共性品格;(2)“体知”是涉及亲身感受之知,不仅强调亲感亲历,而且有亲受之应,即在“为己之学”中实得于己的“自家受用”之处,亦是传统哲学作为修身哲学自我创造性转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所获得的“知识”必能受用以达到变化气质的实际效用;(3)“体知”所知者,主要在于本体的证会,是对人之所以为人的大本大源处的“知”,亦即《大学》“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之“知”。以此三者观之,“体知”不是一个平面范畴,它是一个认识论、工夫论、本体论的立体有机统一体,既是“以身体之”的亲知真知,又是“身体力行”的着实践履,以及“体之于身”而“以天下万物为一体”的生态存在。从“体知”的内涵看,我们也可以把中国古代哲学称作“体知之学”。
二、“体知”之“知”的现代元素
杜先生经常把儒家的人学称作体验之学,过去乃至现在亦有很多人也经常用“体验”来表征中国哲学,那么,为什么要舍其已就而另立“体知”呢?“体知之学”与“体验之学”是否只是床上架床屋上起屋?杜先生提到,“体知”以体验为基础355,显然,“体知”涵括了“体验”的内涵,同时又强调了体验所欠缺的维度。以第一部分结尾由语辨而列出的“体知”三义看,其二、三义项可谓之体验,但第一义项表达了“体验”所薄弱的一个维度:“体验”也是一种“知”,此种之“知”既非仅限于前科学的个人感受,亦非宗教体验中神秘的沟通能力,而是一种更科学的“知”。
至此,借助对“体知”语词表达用法的考察,我们可以回应前面所提出的问题,即对“‘体知’给人耳目一新之感”的辨析。显然,这一感觉对生来其文化即浸润于汉语世界的人有效,而英语世界绝不会有新旧之心理落差。在汉语世界,其“新”之感在于,“‘知’则赋予了‘体’以现代话语色彩,由此,以体验、体贴、体认、体会、体证、体恤、体味、体察、体玩、体究所标志的中国哲学的独特性通过‘体知’进入到现代语境”。356“知”是“体知”的现代元素,“体知”所开出的认识论不再是屈己同人,而是站在西方认识理论发展的前沿成为论说的制高点,同时又不失却自家本来意思,是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得意之作。
返观杜先生提炼“体知”的心路历程,我们能更深入地感受到“体知”所代表的儒学研究上的创造性转化。杜先生以复兴儒学为己任,但却是以很自觉的多元文化背景来反思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这个课题。面对儒家传统失语、无墙博物馆化(museumization)的窘境,杜先生不是简单地从民族感情出发,而是先有一个对中西文化的认真考虑,1962年初入美国学术界,他抱着这样一种心理准备,“如果事实显示,我信以为真的道理业已被证伪,那么我就决不会因此而抱残守缺,甚至会弃之而在所不惜”。357在这一生命碰撞的体知中,杜先生益发坚信儒学作为人学的价值,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传统,是能够发扬广大开来。在当时西方宗教、哲学二分的情况下,东方体验之学由于不合思辨程序极易被归入宗教学,因之“学术界人士对体验之学总抱着怀疑的态度”358,表现之一就是,当时的东方哲学研究大都开设在宗教系。这一东方哲学的观感印象实际上是一个黑格尔式的老调调儿。“我们所叫做东方哲学的,更适当地说,是一种一般东方人的宗教思想方式——一种宗教的世界观”,359或者,儒家传统所讲的做人的道理,超不出常识范围,属日用平常,本无甚可言。中国传统哲学要么被归为浅薄的常识,要么被归为宗教的神秘体验,而总在严肃的学术研究之外。实际上,这一窘境并不由中国传统哲学自身所致,恰恰源自于这一浮浅的哲学、宗教二分:
借用一个吊诡的方式,儒家既不是一种哲学又不是一种宗教,正因为儒家既是哲学又是宗教。如果仅把儒家当做一种哲学,一种理智的思辨,一种纯智的解析,一种逻辑的争论,一种思想的厘清,那么儒家的体验精神就会被忽略;如果仅把儒学当做一种宗教,一种直觉的体验,一种灵魂的信仰,一种绝对的皈依,一种感情的超升,那么儒家的学术精神就会被贬低了。360
有学者评价到,“杜维明先生造出一个‘religiophilosophy’(宗教—哲学)的词来描述儒学,其良苦用心正是力图要在西方学科分类的体制和语境中兼顾儒学的宗教性和哲学性”,361在我看来,其真正的目的,在于重申儒学的活的生命力。在“知识论中占据要津的‘思辨’落到第二义,取而代之的是体验和实践”的时代气息中,重申儒学“体验之学”的价值有了外来上的助缘。在这一新定位中,“体验”一定是可说的,否则此体验只能被归入宗教式的神秘冥悟。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通过现代的语言文字把儒家的体验精神一丝不苟地展示出来?362作为一种积极的反应,“体知”不同于简单的格义或平面解释,而是有其内在的肌理,亦由此故,外在层面的话语系统转换正体现了儒学内在的“创造性转化”。363
这一创造性转化,首在于倡明了“体验”也是一种“知”,且不同于西方传统中源于局外观察者的客观之知,“体知”是整个身心介入的“知”。如对“致知在格物”之“格物”的识解:
不能将“格物”解释成身居局外的观察者对外在事物进行无动于衷的研究。相反,它代表了一种认知方式,认知者在这种方式中不仅被已知事物渗透,而且还被转化了。364
“体知”首先所要极力摆脱的,就是那种认识论上的归约主义,彻底跳出自笛卡尔以来各种排斥性的二分法。体现在身、心关系上,排斥性的二分主张认识系“心”的匠心独运,将“身”在认识发生中的实际作用化约掉。与此不同,体验之知强调“将自家这身入那事物里面去体认”,如明道之“入塔识相轮”而非“对塔说相轮”:
先生尝语王介甫曰:“公之谈道,正如说十三级塔上相轮,对望而谈曰,相轮者如此如此,极是分明。如某则戆直,不能如此,直入塔中,上寻相轮,辛勤登攀,逦迤而上,直至十三级时,虽犹未见相轮,能如公之言,然某却实在塔中,去相轮渐近,要之须可以至也。至相轮中坐时,依旧见公对塔说此相轮如此如此。”介甫只是说道,云我知有个道,如此如此。只他说道时,已与道离。(《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第二上》)
识某物必要身浸入其中,以身体之,否则,所识只是空口之论说,只是“戏论”,只是“玩弄光景”;没有身心上的亲历亲证,它便不能成为真知。但强调“体知”的亲历亲感并不意味着“体知”局限于“见闻之知”,或者说,“体验(之知)”与“经验(之知)”有别。这一点上,西方认识理论研究的新进展能够予我们以支持。自从莱考夫(George Lakoff)和约翰逊(Mark Johnsen)提出embodied mind之后,“具身性认知”(embodied cognition)引起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其中的embodied强调认知与人的身体密切相关,用莱考夫本人的话说,甚至抽象的理性概念最初也源于身体经验的隐喻投射,“我们的身体像什么以及它们如何在世界中发挥作用塑造了我们用以思考的恰当的概念”。365与这一认识论上的新兆相应,有学者断言:“从‘经验’进一步推进到身体性的‘体验’,则不失为现代西方哲学从形而上走向形而下、从抽象走向具体、从玄远纯思走向亲己事实的一种更为彻底的经验主义的走向”,366彻底的经验主义者和中立的一元论者坚持心智和世界都是由“纯粹经验”(pure experience)构成,“这一纯粹经验自身既非精神的也非物质的”,367“体验的视角(embodied perspectives)始于自然与文化是尚未分离、先已存在的实体这一位置”,368而非是两个不连续的实体间的互动。以“心”与“身”的关系而言,心身本就是一,不是二,亦不是二之后的合一,这一观点恰与梅洛-庞蒂在身—心上的暧昧相映成趣。
从“经验”到“体验”这一转变,能够在杜先生英文写作中对“体验”一词的表达选择上体现出来。最初用于表示中文“体验”的是experience(经验)一词,后来受马塞尔(Garbriel Marcel)的启发采用了inner experience(内在经验)369,再后来采用了英文的embody(体验、体现)一词370,显示了体验不同于经验之处。但不同于西方认知科学中向经验的彻底回归以及仅仅将身体看作认知的基础,“体知”还包括其在高认知水平的复杂运作,即“体知”不是认知的低级阶段和前科学的混沌感受性,它有着直接经验性的品格,同时也是“在打破主客对立乃至价值中立的格套之后进行层次较高、方面较多、视野较广的综合性分析”。371借用杜先生解喻“体知”所使用的传统术语,乃横渠的“德性之知”。
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物有未体,则心为有外。世人之心,止于闻见之狭;圣人尽性,不以见闻梏其心,其视天下无一物非我,孟子谓尽心知性知天以此。天大无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见闻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于见闻。(《正蒙·大心篇第七》)
“德性之知,不萌于见闻”,依阳明解释,乃“良知不由见闻而有,而见闻莫非良知之用”(《传习录中·答欧阳崇一》),即“德性之知”涵纳“见闻之知”。一个“梏”字,显示了“体知”(德性之知)可应用于高层次上对事物复杂性的研究,它可以包括逻辑分析一类认知的“隔离的智慧”,在此基础上实现一个更全面的了解和把握。
如此,“体知”作为现代话语,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使此体验之学的生命力透溢出来,但此“新”却是与现代西方理论相砥砺激发而出。亦由此故,“体知”能站在现代话语系统中的优势位置,不再因中国古代哲学缺乏近代笛卡尔式认识论而曲为之说、凑泊缝合,更由于其知“性”、知“天”、知“德”的生活品格而不同于西方纯粹认识论领域中的embodied cognition。“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之“体”,大约是西方人很难肯认的,而这恰恰是“体知”中最具传统特色之处,对此可能性的追究,必然移及“体知”的形而上学根基。


 杨儒宾
杨儒宾